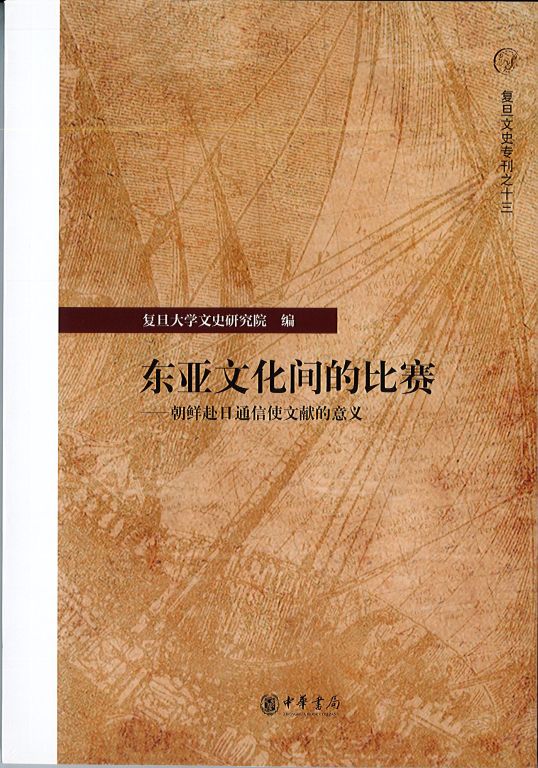
“复旦文史专刊”第十三种《东亚文化间的比赛》
(中华书局,2019年2月)
序
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唯一与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朝鲜,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四十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文献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当然,是研究朝鲜与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很长时间里,它在日、韩学界很受关注,研究论著很多。可遗憾的是,这些文献资料在中国学界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在我们开始整理这批文献的时候,我在网络上反复查询,发现中国大陆学界提及这些通信使文献的论著寥寥无几,而且大都是泛泛而论,或者只是浮光掠影,和日本、韩国庞大而且深入的研究,水准相差太大。这让我想到,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做一个解释,说明这些看上去只是记录日、朝之间往来的资料,对中国学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撰写这些文献的人是朝鲜的通信使,朝鲜的通信使去访问的国家是日本,他们在日本记录的是朝鲜和日本的往来交涉,往来中谈及的也主要是朝鲜或日本的历史人物,那么,这些记载如何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相关?古人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说的是原本不相干,却无端乱关心。中国学界去关注这些文献是否也算“咸吃萝卜淡操心”?在日本与韩国学界,这些朝鲜与日本之间外交使节的记录,长期以来只是作为日朝文化交流史、日朝政治外交史或日朝经济贸易史方面的资料。从中村荣孝(1902-1984)、三宅英利(1925-?)、姜在彦(1926-2014)以下,日韩两国学者有过很多研究,但大体不出这几个领域。因此,在日本学界和韩国学界,确实有人会觉得这些资料似乎与中国关系不大。那么,在中国研究、整理和出版这些文献做什么呢?因此,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的选编过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一些意味深长的地方。自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韩国合作,整理出版了越南、韩国两种燕行文献之后,我们一直在探讨,有没有可能与韩国或日本学校或研究所,继续合作出版通信使文献,但始终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这使得我们无法像前两种文献一样,拿到最好的版本直接影印,只好根据现在能够得到的版本进行标点排印。
不过,恰恰是因为标点排印,参加标点的各位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可以深入细致地阅读这些文献,并按照要求写出详细的内容提要,而收在这本文集中的各篇论文,大多就是他们标点之后写的内容提要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些提要或论文不仅可以帮助读者迅速了解各种通信使文献的内容,也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学者对于朝鲜通信使文献的理解和解说。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献记载的虽然只是朝鲜与日本之间的记录,但它一方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因为在日朝之间的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交往,但也可以看到明清中国在东亚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
现在,《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已经出版,我们也围绕着这个主题,召开了第二次“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讨论会,收录在这里的就是这次会议的若干论文。我希望通过这一文献和论集的出版,推动我们的同仁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如何拓宽史料边界?因为只有新史料,才会带来新问题和新领域,通信使文献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新资料吗?
第二,在东亚的文化史研究中有很多重要话题,中国学者是否也应当参与,并且积极与日本、韩国学者进行对话?
第三,即使是关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是否也可以放在东亚甚至更大的背景中去重新审视,这样是否可以发现很多新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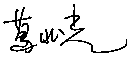
2016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