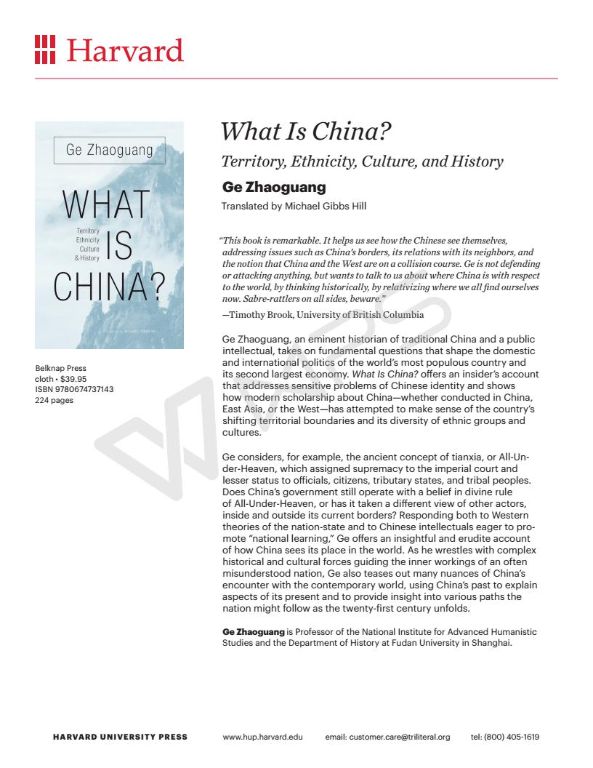
The Report of WHAT IS CHINA i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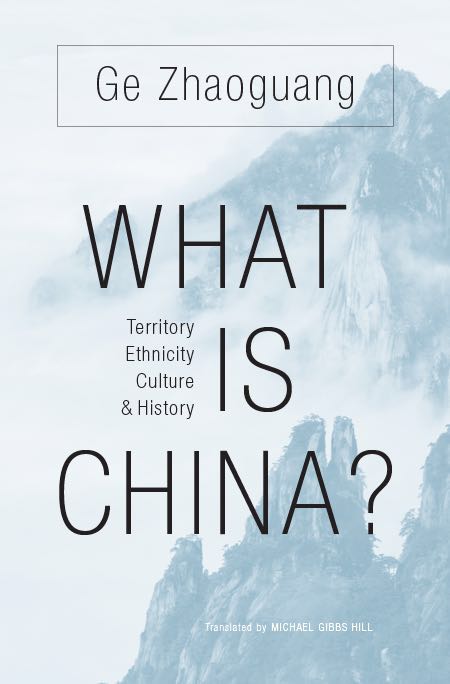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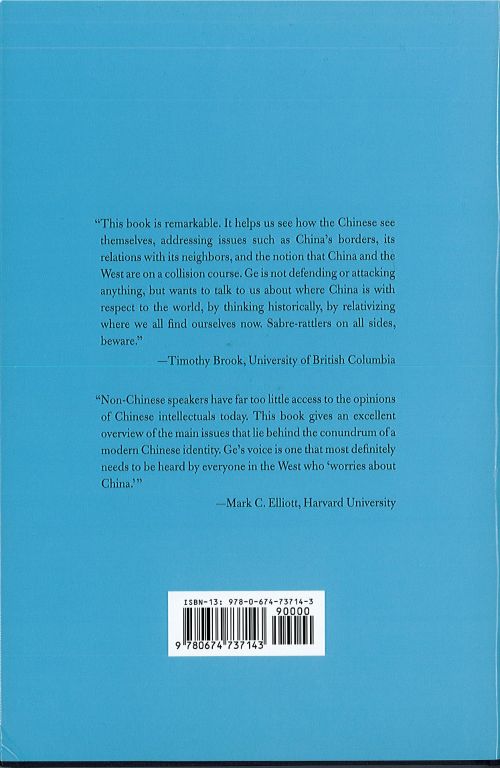
葛兆光教授《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一书的英文版,What is China : Territory,Ethnicity,Culture & History,已经在2018年3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英文本卷首,译者Michael Gibbs Hill撰写了译者序。
这本小书提出的问题,即“何为中国”,如今已经变得日益重要。中国(及其文化与文明)与非中国之间的分野,对东亚政治和历史的形塑,曾经长达数百年。
这种论断也引出了一个简单却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如何定义什么是“中国”与“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是宣称继承了帝制时代中国历史和所谓中国文化的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却聚合了拥有不同民族、信仰和方言的庞大人口。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如何理解这种不同群体的集合?
葛兆光指出,“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意涵是不断变迁的,要避免作一个单一的定义,而如实地讨论这些意涵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产生的背景,将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更好的路径。面对众多热切地解构、甚至消解中国作为历史实体的著述,他将自己的解读视作是另一种选择。
葛兆光的讨论,视野广泛,不仅会吸引关注中国历史和亚洲研究的学者,也会让对国际关系、全球历史和当代事务感兴趣的读者受益。《何为中国》是他第三部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本书和其他一些作品在此之前便已被翻译成日语。《何为中国》吸收了作者前著《宅兹中国》(2011)中的许多观点,以满足更广泛的阅读需求。书中的数个章节由作者的演讲发展而来,因而行文也更通俗晓畅。
《何为中国》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哪怕是在历史学内部,早在2015年春天即已显现。当时中国社科院官方刊物上,曾有一篇文章抨击所谓“新清史”,矛头直指一批在美国研究清代(1644–1911)历史、并且强调这两百五十年间民族、语言和政治互动关系的学者。这些研究者大多不仅使用了汉文档案,更采纳了满洲、蒙古和其他语言的材料。他们的研究成果挑战了很多自17世纪以来便被广泛接受的成见,包括满洲统治者融入中国文化,乃至为之所同化的观点。有关新清史的激辩,展示了清王朝的政治遗产对当今政治敏感议题的重大影响,尤其是有关新疆、蒙古和西藏等地区居民与中亚、中东国家之间的联系。随着共和国与中亚、中东国家贸易与互动的增强,这些问题将持续发酵。
葛兆光采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何为中国”这一问题。作为一位以阅读广博而闻名的历史学家,他使用了数量惊人的史料,这些史料的种类大大超出了自20世纪上半叶,思想史在中国作为独立学问诞生以来所运用的材料范畴。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他都在主张,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应当把常规经典之外的数量庞大的其他文献和材料纳入研究视野。这些材料包括国家颁布的历书、匠作和商业指南、各种图像,以及各种汉语之外的历史文献。
《何为中国》没有掩饰葛兆光对所谓西方理论、尤其是民族国家历史研究者和批评者在中国研究中——它们用英语、汉语和各种语言写成——所使用的理论的批评。在汉语学术机构中,一波又一波西方学术理论和概念框架的涌入,早已被广泛讨论。
可以说,他关注书写中国历史时,与北美、西欧、日本以及其他理论和概念框架的对话,但他却并没有将这些理论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虽然如此,葛兆光的作品显示他非常熟悉北美、欧洲和日本对中国、东亚以及中亚的研究,并能从中引用自如。与此同时,通过对顾颉刚(1893–1980)、冯友兰(1910–2005)、李济(1896–1979)等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的讨论,他也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早一辈的思想家,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理论涌入之前,思考有关民族、国家等问题的。
《何为中国》的导论部分,向读者概述了不同的学派对“中国”意涵——诸如“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民族集合体,以及一个基本的历史研究框架——的挑战。作者反驳了一些在他看来言过其实的论断,诸如中国乃是一种想象和建构;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纠正有关中国的过去是单一历史构建的言论。
第一章回顾了相关观念——即中国(“中央王国”)与更广阔的世界的关系——的演变。他详细阐释了认为中国占据文明中心的复杂的“天下”观。本章使用了大量史料,包括地图、考古发现、故事与传说,以及经常被儒家导向的思想史研究所忽视的佛教文本。虽然最终回到了中国从“天下”中心转向“万国”之一的老故事,但他指出了中国历史中存在的其他一些可能性,尤其是将印度作为宗教世界中心的佛教世界观,这些可能会推动中国天下中心的观念,走上新的方向。
在第二章中,作者对于中国历史上疆域与主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中国”作为“诸国”中一国的观念,早在宋代(960–1279)就有大量的先例。北宋时期,“中国”不断面临着北方族群(如女真人)的压力,而最终大片国土也丧于敌手。相比近代早期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中国”意识到自身国家结构和民族特性有别于他国的新观念,出现的要更早。
虽然葛兆光承认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历史困境——这正是清代大规模的领土扩张的遗产,但他也指出,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周边疆域问题的学术讨论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尤其是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企图,是难分难解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以及中国对满洲、蒙古和西藏主权的继承提出质疑,这与日本对上述地区施加影响、乃至直接占领的企图,有着直接的关联。
第三章讨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作者敏锐地指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考虑这些问题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大致包括呼唤革命的“驱逐鞑虏”、孙中山(1866-1925)提出的“五族共和”,到更晚一些学者对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其研究与避免外族入侵、维护中国完整性的现实需要之间,尽可能地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可能的话。而到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边疆地区面临外敌入侵的直接威胁,学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张达到了高峰。
葛兆光对于顾颉刚创办的《禹贡》(英文名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始终给予极高的关注。他不仅仅将之视作历史材料,更把它运用于解决中国历史所面临的挑战,这也正是整本书在探讨的话题。为这份杂志撰稿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命运与遭遇,向我们展现出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国际局势对其研究方向产生的持续影响。举例来说,费孝通有关生活在遭受日本人统治或威胁地区的少数民族,可能不是大中国或中华民族之一部分的论调,便受到了学术同僚的猛烈批评。尽管作者没有直言,但在我看来,他事实上指出了,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应当从历史的框架中去观察,在讨论当前问题时,应回顾早期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第四章中,作者谈论了对历史上中国文化“复数性”的理解。尽管他将一系列定义中国文化的特征聚焦在汉族之上,但他也指出,很多其他民族也曾不断地对汉族的文化特征产生影响,尤其是宗教和物质文化。作者对于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强调,也回击了一些宣扬复兴(单一的)中国文化的新传统主义论调。这些人忽略了中国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多样性,而轻易地陷入了汉族沙文主义,乃至盲目的大汉民族主义之中。在作者看来,这既是对历史的错误阐释,也是对民族国家理论的误用。
在第五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日本和朝鲜的汉文史料、从中国邻国的历史文献中去反观中国自身的历史。这些材料中有一点信息是十分明确的:自明朝覆灭,日本和朝鲜的高级知识阶层与清帝国有所接触后,开始认为,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其不再具备自称天下中心的资格。他们中的某些人逐渐将自己视作汉唐传统的继承者,尤其是在新儒学思想方面。葛兆光指出,十七世纪在东亚历史上是极具转折性的关键时刻,明王朝的覆亡以及西方影响的渗透,使得日本、朝鲜在政治和文化上不再认同中国。就当下来看,这些来自日本和朝鲜的、对中国不断变化的观点,也对我们旧有的历史观点——无论是大众意义的,还是学术意义的——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从历史来看,那种单一的、不变的中国文化并不存在。
最后一章探讨的是,全书所涉及的各类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日渐加重的角色之间的纠葛。作者指出,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具体来说是传统中国儒释道的和谐共生,或许能够为世界的未来提供新的选择。与此同时,他警惕和反对复活某些过去的观念并施用于现在的中国,尤其当中国在世界上已有如此地位之时。举例来说,重提“天下”观念并以此解释中国的对外政策,或许在某些时刻、某些方面是有效的,但这种做法也会给一种新的中国例外论提供依据。这将会违背现有的标准与规范(尽管它们确实没那么令人满意),而去追逐一套危险而尚不明确的新秩序体系。
*******
《何为中国》中的许多关键概念,都在不同语言和思想体系之间的文本翻译、同意转换和表达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对于译者而言,即便是China这个单词,虽然被许多语言使用,但并非总能与中国统治者书面语和口语中使用的词汇准确对应。比如,清朝在书面语中自称大清国,而不是中国在使用“中国”一词时,葛兆光经常加引号,以引起人关注其可能的意义以及对这些意义的争议。他的用法迫使译者不断调整,选择最好的形式来传递他的意图。当我不用China,采用“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或“中土”(Central Land)来翻译“中国”一词时,我会在括号内标注拼音,以免读者产生疑惑。
作者经常会使用“四夷”(Si Yi)这个词,“四夷”常被翻译为四个方向上的四种野蛮人(“four barbarians”),也可取更偏中立的含义,指代非汉民族;“夷”和“蛮族”的对译,曾经引起清朝和大英帝国间的外交纠纷[ 参看Liu, Clash of Empires, 31–69.]。其他翻译包括“外族”或“四方民族”。我将这个词语翻译为“four barbarians”,因为在我看来,《何为中国》在使用词语“四夷”时,是充分了解其历史意涵的:理解中国边疆的意义,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研究这些地区及其居住者时,运用一系列新的标准,去取代那些传统汉语叙事中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上的等级序列)。
我尽可能从现有英文译本中摘取现有的译法,尤其当这些译法可以向不懂中文的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和背景时。我仅在非专业读者可能不熟悉的术语或参考文献之处添加译者注,以指明我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使用过的其他资料。
非常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克鲁格中心容许我在这里完成译本的最后润色。Wu Xin为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建议,Mark Kellner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历史词汇的日语翻译和音译。葛兆光慷慨回答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史料来源方面的问题。另外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为本译本提出许多改善建议。译本若有任何错漏之处,皆由译者负责。
(注释从略,详注可参见附录)
(裴艾琳译,张佳校)
译者序链接:《何为中国》译者序(张佳修订稿).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