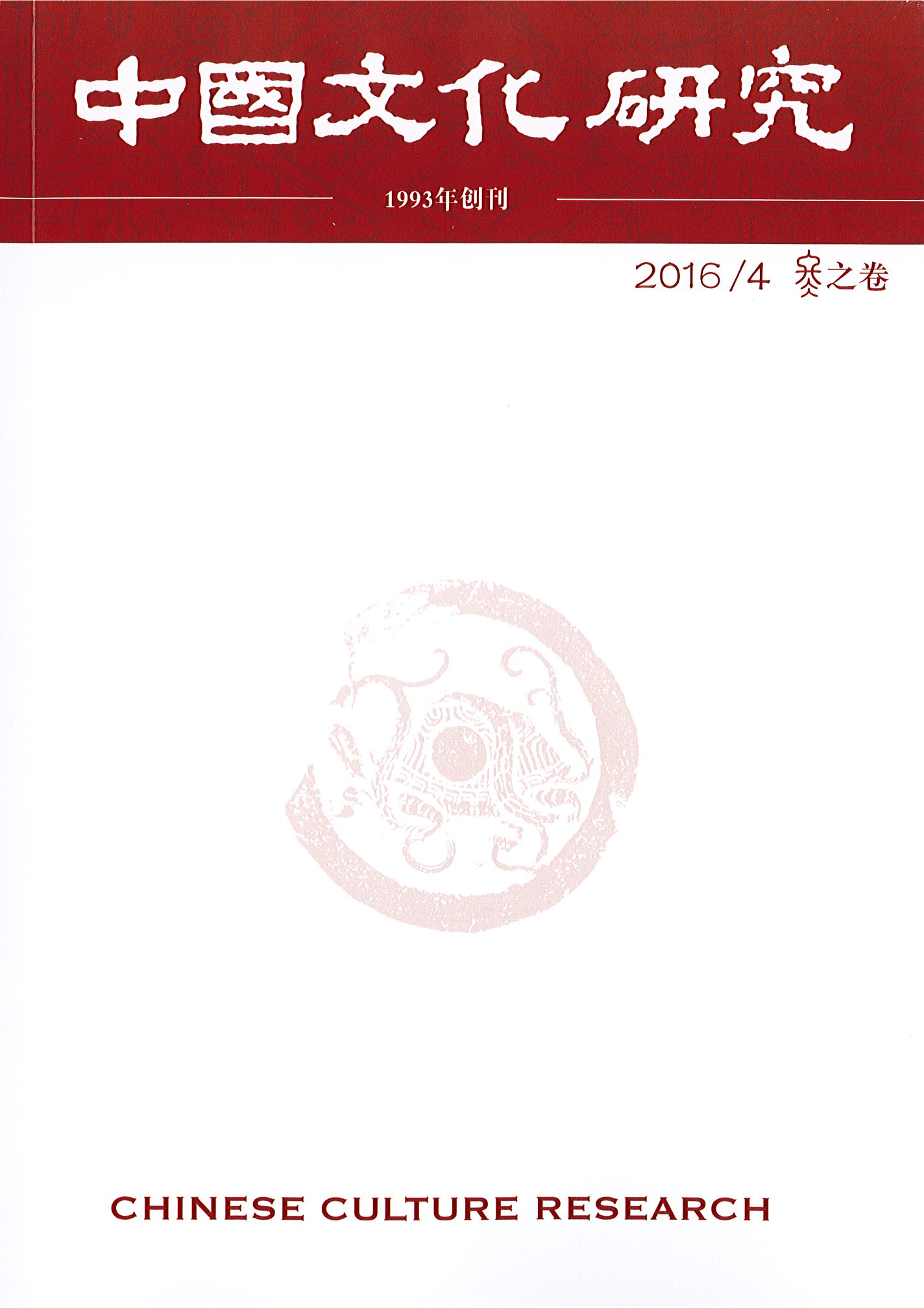
《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刊载葛兆光教授主持专栏,专栏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包含4篇文章:葛兆光《在“一国史”与“东亚史”之间——以13-16世纪东亚三个历史事件为例》、段志强《“中区”与王夫之的中国观》、钱云《宋代“御戎论”的传播与意义——从科举用书谈起》、林磊《“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命运——以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为中心》。
主持人语
葛兆光
这里的四篇论文内容不同,却有一个不很明显的共同主题,也就是讨论“东亚”与“中国”。我们很难把这些论文简单地归为“政治史”、“史学史”或者“观念史”的传统学科范畴中。表面上看来,葛兆光讨论一国史和东亚史的差异,大致可以算史学史或者史学方法,但是他想说明的却是,很多历史事件犹如草蛇灰线,东山钟鸣,西山磬应,虽然表面只涉及某一两个国家,实际上却会对整个东亚区域都有影响,如果忽略这些“外面”的或者“边缘”的历史事件,可能并不利于理解一国的历史,因此历史学也应当超越国境,适当考虑东亚历史彼此交错的可能性;钱云讨论宋代“御戎策”的普及,一方面关注的是宋代由于处在汉唐所未曾有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刺激了宋代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一方面引入印刷、科举等现在叫作“新社会史”或者“新文化史”的角度,思考这种精英士大夫的国家意识怎样成为一般民众的“常识”,从而重塑了传统时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图像。或许,这一研究可以算在观念史中,但显然其中又融入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段志强关于“中区”的讨论像“概念史”,虽然说的是来自明清之际王夫之的一个概念,其实,他要讨论的还是关于传统时代人们如何认识“中国”。王夫之所谓的“中区”,一方面来自古代中国人关于华夏山川地形的认知,一方面与明代甚至明代之前传统帝国的实际疆域相关,这篇文章有趣的是,指出这一观念居然还和“堪舆”也就是风水知识牵连,或者应该反过来说,连风水知识也受到“中区”这一观念影响,特别是,这种把“区”局限在这一疆域的思想,如何与清代多民族大一统帝国状况不合,这给后来民族主义带来思想资源,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说,这是“概念史”的梳理,但是这个“概念史”已经超越了传统精英思想的范畴;最后一篇是林磊讨论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史学家在抗战时期有关历史学意义的思考,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抗战期问,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书生何以报国”成了史学家心目中的大问题。原本提出“史学即史料学”,希望把历史学建没成像地质学、生物学等科学一样严谨、客观、中立的学问的傅斯年,为什么在抗战时期会转而成为倾向民族主义的史学家?而且这一转型正是国族危机下的很多中国学者共同取向?这当然是一个史学史的话题,也是思想史的话题。
近年来,有关“东亚”和“中国”等课题,以及有关疆域、民族和认同的研究,毫无疑问,一方面受到全球史、区域史等新取向的影响,一方面也来自对于中同在东亚和世界的处境的刺激,由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这些话题逐渐被学界关注。这里发表四篇论文,同绕着这些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讨沦,其实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在“一国史”与“东亚史”之间——以13-16世纪东亚三个历史事件为例
葛兆光
提要:
这篇文章选择13 - 16世纪发生在东北亚的三个历史事件,也就是“蒙古袭 来”(1274 1281)、“应永之役”(1419)和“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7),来讨论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差异。本文指出,如果仅仅站在一国历史的立场、角度和视野来观看发生在东亚的历史,会出现“角”或“盲点”。因为,只有一个圆心(国家)的历史叙述,会使得历史有中心有边缘,中心虽然清晰,但边缘常常含糊甚至舍弃。其实,边缘的历史未必不重要,如果历史叙述有若干个圆心,形成多个历史圈,在这些历史圈的彼此交错中,就会有很多重叠,这些重叠的地方就会显示出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让我们重新观看历史。一国史可能会忽略这些边缘,而东亚史可以凸显几个历史圈边缘的交叉。
关键词:蒙古来袭 应永之役 壬辰丁酉之役 国史 东亚史
引言:东亚的三个历史事件
对于近世东亚史,特别是13世纪之后的历史,有一些事件对一国史的重要性不一定很大,但对于东亚史来说可能相当重要。
其中,我想选择三个事件进行讨论。第一个是“蒙古袭来”(1274,1281),第二个是“应永之役”(1419),笫三个是“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7)。由于这三个事件都涉及东亚中日韩三国历史,所以,观察作为一国史的国史著作如何描述它们,从中也许可以看出“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发现,仅仅偏执于各国立场的书写,可能会出现一些历史的“死角”和“盲点”。
下面,我选择在中国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国史著作,如(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2)范文澜《中国通史》(后数册为蔡美彪等著)、(3)郭沫若《中国史纲》、(4)白寿彝《中国通史》,同时参考其他一些大陆、台湾、香港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通史著作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中区”与王夫之的中国观
段志强
提要:
王夫之用“中区”的概念描述他心目中的中国。中区是由山川、海洋、沙漠等一系列自然界限所围定的地理区域,大致相当于明代的两京十三省的范围。中区的概念渊源于以山川定义华夏的传统,也与堪舆术中地气的理论有关,这是一种超越了王朝和正统观念的中国观,但与清代以来的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国家观念形成对立,并曾成为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渊源之一。
关键词:王夫之 中区 中国观
引言:
以地理环境来说明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者用地理因素解释中国文明何以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的局面,是史学家常用的论述策略。这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中同地理环境“四面受阻”说,代表性的阐释如“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因为这种地理上的特点而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在此范围内中国文明具有向心性和凝聚力,利于长期延续,二是历史中国也很难逾越此一范围而向更远的地方扩张。本文尝试从王夫之(1619-1692)的“中区”概念出发,讨论上述看法的历史渊源,并重新评估其意义。
宋代“御戎论”的传播与意义——从科举用书谈起
钱云
提要:
宋代中国是古代中国重塑对外秩序的重要时期,政治格局的改变无疑影响了宋代精英士人的对外思想与理念。本文将讨论的是,上层精英对政治局势的直接讨论,如何经由科举制度及其衍生品科举用书,使得在政治新形势下产生的现实主义对外观念与传统世界秩序理念一同成为一般知识阶层的知识与观念,并且如何参与重塑宋代中国人知识与思想中的世界秩序。
关键词:科举用人 宋代 对外观念 “御戎论”
引言:
北宋至和二年(1055)五月,欧阳修曾上奏著名的《论雕印文字札子》: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实证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
在欧阳修的这份札子中,以时文集《宋文》(即《宋贤文集》)为例,说明(1)虽热朝廷屡颁禁令,但是书商为了经济利益往往钻其漏洞,肆加刊印文章选集;(2)书商为迎合、占领市场,常选编“当今议论实证之言”,因而将朝廷动态、朝臣言论泄露于庙堂之外,更因为书籍行销面广,甚至可能令有关言论泄露至境外;(3)时文集所编选的文章,可能过度注重时效性,而对文字章法不太重视,不足为应举士子师法。
前人研究中,多有关于欧阳修的这份禁书札子的讨论。总体而论,前行研究已经注意到,两宋时期相继与辽、金、蒙古的长期对峙,不仅在政治、军事等逐渐确定彼此的边界,双方也通过书禁(以欧阳修为代表)确立文化的边界。但是,在科举发展的背景下,书商们纷纷选编与整理的时务文章,就将朝堂言论对一般知识阶层开放,实际上打通了普通读书人窥测朝堂之上对外政策的渠道。所以,如果将对禁书的考察视角从域外转向域内,除了防止直接向敌国泄露言论之外,这些书籍在国内广泛流布也同样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因为一旦相关文章在域内广泛流传,扩散了精英阶层对外知识与观念,增进了一般读书人对于当时“国际”政治秩序的知识与理解,但也不免增加了流向域外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时务文章成为科举用书的重要内容,就使精英阶层的现实政策成为共识性知识,从而影响域内的政治、文化舆论,也重塑了宋代中国人的国家、世界观念。
因此,本文将从域内视角对科举用书中有关域外的信息、言论作一整理,以期说明宋朝政治、文化精英对政治局势的讨论,如何经由科举制度及其衍生品科举用书,成为影响一般知识阶层的知识与观念。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命运
——以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为中心
林磊
提要:
如果说史学在近代中国挣脱经学枷锁的历程是一种“独立”,那么必须看到“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的杠杆作用。这种制度化、专业化的近代史学也只有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抗战时期的傅斯年即面临这样的境况,如果科学的历史研究丝毫无助于民族存亡,那“史之为道”其用何在?但在以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召唤起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同时,如何防止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在人群中制造分离和区隔——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构成威胁?傅斯年选择以“建构国族”的方式从“民族国家”的概念中拯救“中国认同”,但却落入“民族”二字的语词陷阱而不自知,完全忽略了“国族”仍旧是“民族”的一种,比它想去替代却又自其脱胎的“民族”更缺乏实在感和安全感。
关键词:民族主义 傅斯年 《东北史纲》 《中国民族革命史》 大泰唯国主义
引言:
如果说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标志的晚清史界革命,重在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以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为标志的五四新史学,重在示范“如何研究历史”,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代表的史观学派强调”怎样解释历史”,那么日本的侵华,则促使史家开始重新思考“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所谓“重新思考”,指的是回到1902年梁启超揭橥的史学用以发达民族主义的命题。只不过梁氏的民族主义史学意在塑造新民,可称之为“民族进化之学”,而抗战史家的民族主义史学意在凝聚国族,因而是一种“民族认同之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傅斯年这个受“学术民族主义”激荡,为把“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建立在中国而矢志要将“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剔除于史学之外、把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史料学派领军,自觉地转向了一种强调国家至上、立意正大的“民族主义学术”。本文想通过抗战时期傅斯年对中国疆域和民族问题的思考与诠释,来讨论新学术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话语与传统历史意识之间的紧张如何塑造史家,为研究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时代重负下的志业与命运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