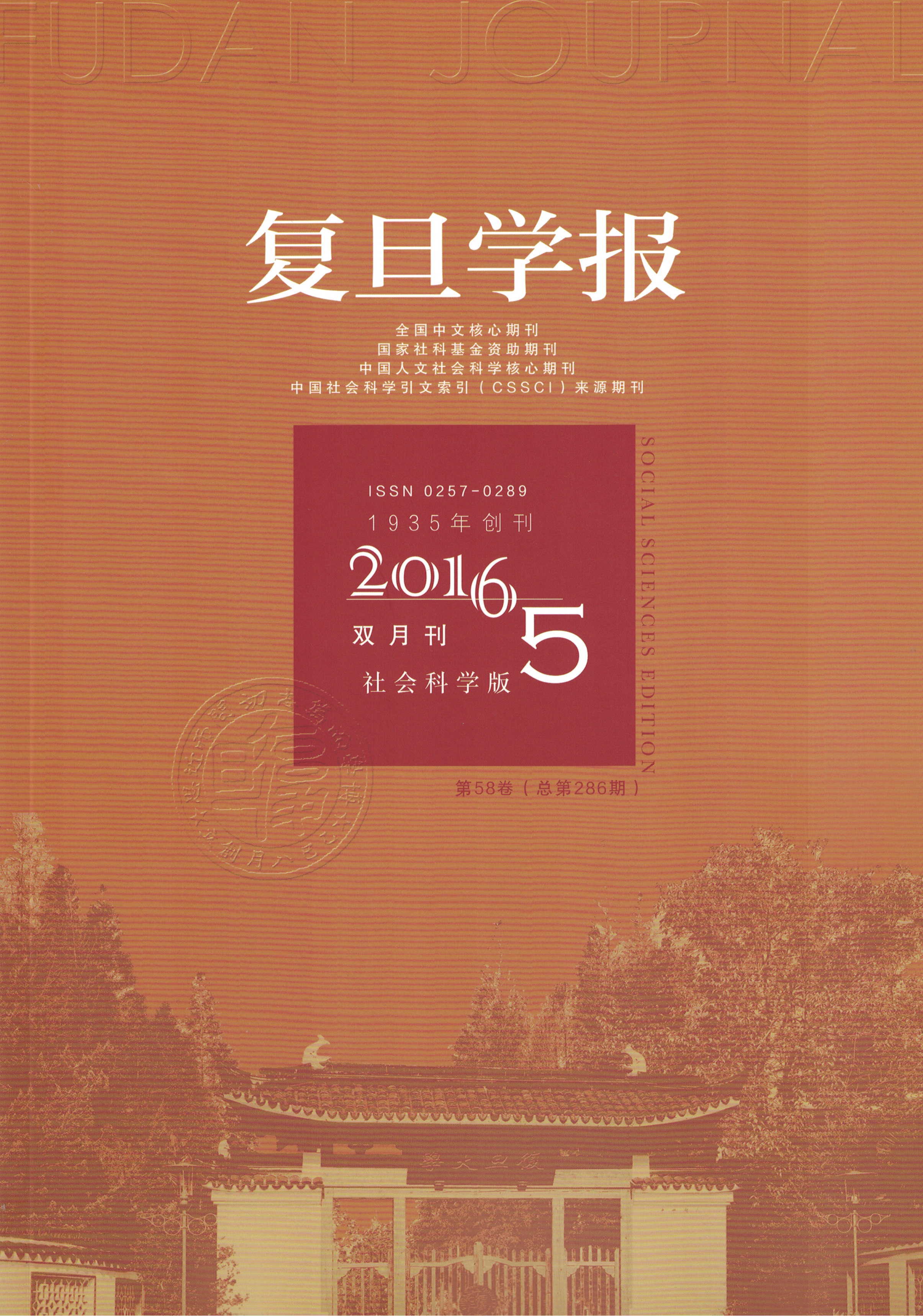
《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刊发葛兆光教授主持专栏,专栏主题为“历史中国之内与外”,一共包含6篇文章,分别是1)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从“周边看中国”到“历史中国之内与外”》;2)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中国民族与民族史》;3)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华帝国体制的内轻外重》;4)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华文明的“内”与“外”》;5)王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研究科)的《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同心圆》;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边疆结构与“历史中国”认识》。

我想在这里先交代一下“历史中国之内与外”这个研究主题的由来。
十年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曾提出一个题为“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计划,试图尽可能改变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自说自话的固执习惯,也稍许改变仅仅从近代欧洲历史进程与文化观念来反观中国的单一尺度,更希望努力实践胡适1938年参加世界历史学会时提出的,把日韩保存的有关中国史料作为“新材料”的想法。所以,从2007年以来组织整理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朝鲜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和《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等有关中国的域外文献,我个人也出版了《宅兹中国》、《想象异域》等论著,还组织召开了几次有关“从周边看中国”、“东亚海域”、“亚洲历史与民族认同”的会议。也许“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计划,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多多少少刺激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转变。
但在有关“从周边看中国”研究的各方面评论中,我也注意到各种质疑的声音,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质疑。这些质疑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周边”?“周边”是环绕现代中国的异国吗?“从周边看中国”是否仍然隐含了以中国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中心主义?在这里,一个最不能不回答的问题是对“周边”的界定。简单地说,如果按照现代中国国境来说“周边”,“周边”当然只能是日本、韩国、蒙古、越南、缅甸、印度、俄罗斯等国家。但是如果按照历史上的帝国或王朝疆域来说“周边”,那么,除了历史上相对稳定延续的汉文化核心区域——尽管也充满复杂的族群融汇与交错,我仍然坚持“中国”有相对稳定的核心区域——之外,满蒙回藏苗彝等相当多的族群和区域,在历史上是否也是“周边”?我们是否也能从他们的立场和视角,来反观核心区的“中国”?由于这在中国大陆不只是学术领域的历史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些年来我们只能比较含糊笼统地使用“周边”这一概念。
可是笼统含糊只是权宜之策,如果不断追问,不仅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问题,可能也会涉及更多学术问题。比如说,如果按照现代国家的国境来说周边,这种“周边”只是“外”,涉及“中国”与“周边”的历史研究,只应当算在“中外关系史”领域。可是,如果按照传统王朝的疆域来说周边,这种“周边”如今可能是“内”,涉及这种“中国”与“周边”的历史研究,就往往算在“中国民族史”领域中。可是由于历史中国无论在疆域上、族群上和文化上,都是移动的和变化的,“内”、“外”之际会移形换位,因此,我们不得不在“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之后,再推动“历史中国之内与外”的研究。我希望在这一研究中,不仅说明历史中国的疆域、族群和文化之内、外变化,改变某些有关“中国”与“周边”的固执观念,也试图沟通和融合中外关系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各种资料、理论、方法和观念。
因此,我们从2016年开始推动“历史中国之内与外”研究计划。3月中旬,我们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中心支持下邀请了一些学者举办workshop,在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上,我们首先对边疆、民族,以及民族史等问题进行讨论。下面刊登的几篇笔谈,就是根据各位学者的发言整理而成的。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些笔谈涉及面很广,各自观察角度也不同,讨论的立场与焦点也各有差别。这促使我们思考,也许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逐渐把问题整合与聚焦,对“历史中国之内与外”作更深入的讨论。
全文下载.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