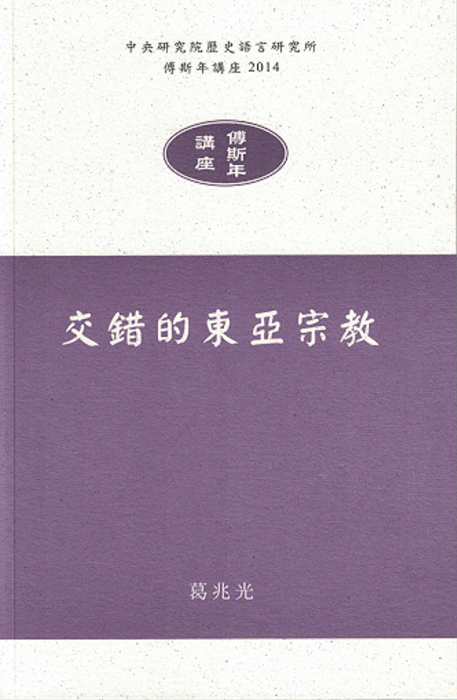
葛兆光 著《交错的东亚宗教》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8月
自序
这本小书收录的是2014年10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讲座”的三篇演讲稿。前两篇是正式演讲,主题即本书书名:“交错的东亚宗教”。在这个主题下,我从涉及东亚的佛教史和道教史中,各选了一例来讨论。《回应西潮》这一讲从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中国与日本的不同表现讲起,讨论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当时席卷世界的西洋潮流冲击下,由于各自国家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形成了回应西潮和现代转型的不同历程,也导致了现代中日佛教的不同命运,其实,我也想借这一历史现象,重新检讨东亚近代史上的“冲击-反应”模式,对这个看似过时陈旧、却仍有生命力的理论,作一些修订与补充;《橘枳之异》这一讲,则选择了古代中国道教在古代东亚即朝鲜与日本的流传问题,对宗教史上的所谓“影响”与“传播”,尤其在“概念”、“立场”和“方法”方面进行了检讨,意在通过道教在东亚的流传,说明宗教传播史研究中,重要的是说明流传过程中的变异,以凸显受容一方文化的改造与诠释力量。最后一篇《纳四裔入中华?》,是作为第三场座谈会的讨论文本散发的,这是我最近特别关心的话题,即如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中华民族”。在这次座谈会后,此文已经发表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思想》杂志27期,之所以要在“傅斯年讲座”特设的座谈会上讨论,是因为我特别期待听到台湾学界的意见。
整个2014年春天和夏天,我都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原本访问哈佛大学的意图,是在那几个月里休息和放松,因为前些年太累了。但这几个月中,大部分时间我却不得不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为这次“傅斯年讲座”准备讲稿。我记得,在与黄进兴所长商量演讲题目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想讲《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有关禅宗史的研究方法》以及《预流的学问;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东方学研究之潮流》这两个题目的,因为我觉得,胡适与陈寅恪都与中研院尤其是史语所有关,但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改讲“交错的东亚宗教”为好。事后再细细回想,之所以我会反复思量并改变主题,而且要用那么多时间来准备讲稿,不外是三个原因——
首先,“傅斯年讲座”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重要的纪念性讲座,傅斯年先生本来就是我尊敬的学术前辈,特别是当我受命创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创办史语所的思路、原则和途径,就更是我所追踪和效法的榜样,有机会担任这一讲座表达我对傅斯年先生的一点敬意,自然不能不用力用心。
第二,史语所是我很佩服的人文学术机构,自从傅斯年先生1927年创办以来,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镇,所内高手云集,各个领域都有专门研究者。在这样的讲坛上演讲,正如当年钱钟书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诗可以怨》时,一开始所说,在这种群贤毕至的场合演讲,即使不是赵子龙一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才行。因此,我不能不谨慎从事,认真准备。
第三,很长时间以来,我曾经涉猎过一些佛教史与道教史,虽然不算本色当行,也算略知一二,自己觉得,多年来也掌握了一些资讯和文献,总觉得无论在佛教史还是道教史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发掘的缺漏环节和值得反思的研究方法。最近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大陆倡导“从周边看中国”领域的研究,多少又关注一些历史上东亚诸国的互动,这次以“交错的东亚宗教”为主题,其实就是想把“宗教史”和“东亚史”两方面的知识与思考交汇在一起,以期引起学界对东亚各国之间宗教交流史的关心。我觉得,这一领域还有相当多的概念、立场和方法上的问题,值得学界深思。
演讲结束,自觉还算不辱使命。此番台北之行,要特别感谢历史语言研究所,感谢黄进兴院士的盛情邀请和亲切接待。同时,也感谢王汎森、邢义田、杜正胜、林富士、李贞德等各位教授,感谢你们的倾听、讨论和主持。特别要感谢的,是余英时先生和张广达先生,在写这两篇演讲稿的时候,我曾去普林斯顿看望余先生,并把两份讲稿呈交余先生批评,得到了余先生的热情鼓励;张先生则是我大学时代修习中国史的老师,这次他特意前来,让我在感激之外,还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自己感觉就像回到三十五年前北京大学的课堂,学生再一次静候老师的测验和考评。
是为序。
2014年12月30日于上海复旦光华楼
【目录】
自序
第一讲:回应西潮——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前后的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
引言:从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说起
一,“世界宗教大会”上的儒家与佛教:中国与日本之差异
二,左手世界主义,右手国家主义?日本佛教对西潮的应对策略
三,反应迟半拍:晚清民初中国佛教的左右为难
四,亡羊不能补牢:后发的中国佛教之现代困局
五,同途殊归:晚清中国佛教与明治日本佛教的不同命运
结语:三面受敌的现代中国佛教:西潮、居士佛学与日本佛教
第二讲:橘枳之异——东亚道教交流史之概念、方法与立场的再思考
引言:关于东亚道教研究的问题
一,祓除祭禳仪式、符咒法术与“守庚申”习俗:东亚的中国道教痕迹?
二,时代和路线:中国道教在东亚之流传史
三,“外来”抑或“自生”,“影响”还是“借用”:对于道教在日、韩流传与遗迹之再评估
结语:关于东亚道教研究的概念、立场与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或“不是”?
【座谈会·附录】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
引言:现代中国如何形成国家:“从天下到万国”与“纳四裔入中华”
一,“五族共和”与“驱逐鞑虏”:晚清民初“中国”重建的不同思路
二,“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的新取向
三,“本土的”与“复数的”: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学界对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取向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1937年前后中国学界心情的转变
五,“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年《益世报》上的争论及其他
结语:“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中华民族论
【提要】
第一讲《应对西潮——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前后的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提要】
18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事件,它冲击着世界各种传统宗教。日本佛教徒对于这一现代潮流早有准备,在会议上应对自如,说明日本佛教已经走出明治初年“祭政一致”和“神佛分离”造成的困境。但是,与日本不同,代表中国出席大会的主要是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与会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彭光誉,则以帝国官员与儒家学者身份,傲慢地坚持儒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宗教”与“现代”都表现出相当不屑。中国佛教不仅缺席大会,并且在那个时期,对现代潮流也缺乏回应,虽然1895年之后的中国士大夫转手从日本学到佛教在现代的种种意义,因而刺激了晚清佛学复兴,但中国寺院佛教对西潮的反应,仍然慢半拍甚至一拍,直到“庙产兴学”直接威胁到佛教的生存,才开始了佛教振兴与佛教改革运动。然而,正是由于中国佛教的反应迟缓,使后起的中国佛教不得不面对居士佛学的挑战、现代政治和思潮的压力和日本佛教争夺空间的三重压力,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举步维艰。对比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这一现代历史过程,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有关东亚、宗教与历史的问题,检讨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讲:《橘枳之异——东亚道教交流史之概念、方法与立场的再思考》【提要】
这一讲的问题意识,来自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道教在东亚流传与影响的研究现状。如何评价中国道教在东亚的影响与传播,日本、中国与韩国学界曾有激烈争论。本文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道教遗迹”的若干现象为例,指出古代的中国与韩国、日本之间,自从古代巫觋、秦汉方士、中古道教以来,曾有着一波又一波的交流并留下文化遗迹,对这些文化遗迹,笼统而简单地说它“是”或“不是”中国道教的影响,其实不仅受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感的影响,也往往忽略历史上这些文化遗迹的叠加过程。特别是,如果我们仔细清理中国道教在日本与韩国的流传,特别是十一世纪之后的流传,就能知道道教在东亚的流传与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形塑下,不仅在各个时代不同,在各个国家也不同。本文意在说明,超越国家/王朝的宗教史研究,不仅要说明文化之间的“交错”和“叠加”可能塑造了一个彼此相近的“东亚”信仰世界,更要说明的是,道教的流传与影响,在中国、日本与韩国不同背景中,曾经发生移形换位的变异。
【座谈会·附录】《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提要】
这是一篇历史学论文。之所以要特意强调这是“历史学”的论文,是因为本文对现代中国的国家,特别是它的疆域和族群,只是试图客观地描述一个历史过程,即描述现代中国及其疆域、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如何,甚至只是在描述这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即1920-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主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如何参与重建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叙述,而不是在对这种国家形态的形成过程作任何价值判断,我既不是在为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也不是在为现代中国面临的“内”与“外”的多重困境开药方。因此,这篇论文叙述的只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从晚清以来,特别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这二十来年中,中国主流学界是如何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刺激下,参与到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论述的大潮中,在学术上努力纳“四裔”入“中华”,也许,这一努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现代“中国”这个在疆域与民族上都颇为特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