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兆光教授《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发表在《中国文化》2012年秋季号;《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发表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读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发表在《南方周末》2012年9月6日“阅读”版。以下为文章节选(《南方周末》一篇为全文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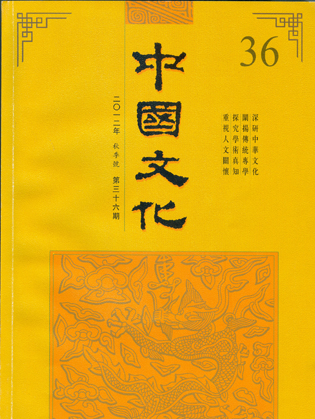
《中国文化》2012年秋季号
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
葛兆光
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东京召开的“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五
全球史写作往往针对的是文明史而不是政治史。也许,很多学者觉得,由于文明与国家并不一定在空间上重叠,所以,不必固执于国别史的研究和写作。可是,怎样的一个“全球史”可以去除“国别”而聚焦于“文明”?这种去除了“国家”的“文明史”如何撰写?…
我赞成全球史的写作,但不必因噎废食,把国别史看成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或者无用的历史叙述方式,特别是在重写政治史的时候。因为下面三个原因需要格外重视。(一)在历史上,由于有的区域,其疆域、民族、文化以及政治相对稳定在一个“国家”/“王朝”/“政府”之下,因此,它仍然是一个自足的“历史世界”,国别史仍然较容易呈现其历史状况与现实特征。(二)联系的全球史,在交通阻隔、车马不便的时代,人口、民族、宗教、文化没有太多联系,历史学家很难写彼此关联的历史,只是到了海陆交通发展,文化交错的空间越大,这种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才会越大,不必一概而论地追逐全球史而忽略国别史。(三)当一个国家现在处在政府力量仍然强大、国家控制相当严密、意识形态依旧笼罩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追溯这种传统、这种观念、这种制度的来源,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不能不注重彼此区别的“国别史”。
当然,我要郑重说明的是,这个“国别史”的历史叙述空间虽然是“国家”,但它并不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来倒推“历史”,因此,它不一定要像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的那样,需要“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只要这个国别史中的“国家”并不固守一个不变的边界来叙述故事,也不把“历史”限制在一个从现代国家逆向追溯出来的边界之内。比如中国史中的“中国”,我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已经指出:“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更何况这个“中国”中的王朝、族群、边界始终在历史中交错与融汇。
所以我想,如果国别史的撰写者,看到“民族”和“国家”本身的历史变迁,就不会落入后来的“国家”绑架原先的“历史”的弊病之中。这样,国别史的书写就仍然有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
葛兆光
引言 为什么要和博士生讨论“学术书评”?
之所以要讨论“学术书评”这个话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而借题发挥或蜻蜓点水的评论风气渐盛。对于书籍借题发挥的评论固然不应厚非,但是那不是真的评书,也比较容易写;严肃的、裁断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学术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们将来是要做学位论文的,而大学里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严格要求的话,通常要有一章(或者一节)“研究史”,就论文涉及的这个领域,业已出版的各种论著,做一个述评,说明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遗漏和缺失。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对各种论著的短评的汇集,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本科,甚至硕士、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都不够重视。…

《南方周末》2012年9月6日
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
——读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
葛兆光
危机当头,学术不能置身事外
九一八事变(1931)与伪满洲国(1932)建立之后,整个中国都在风雨飘摇之中。1934年,顾颉刚和朋友们在北京创办了《禹贡》半月刊,虽说是讨论历史和地理,但心中想的却也是民族和疆域。在发刊词中,顾颉刚针对日本分割中国边陲与分化中国民族的论述,痛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停刊后,1939年顾颉刚又为《益世报》办了“边疆附刊”,在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他再度聚焦民族和边疆问题,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希望人们不要太注重汉、满、藏、回、苗等等区别。为了在危急时刻重建国族认同,他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疑古主张,对可能启发过他提出疑古思想的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进行批评。
与顾颉刚一直有分歧的傅斯年,虽然主张在国家危机的时候,不要轻易地谈“民族、边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词”,但也对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的观念表示赞同,觉得他“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并痛斥一些民族学家拿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当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进行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
联系到傅斯年曾撰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学者矢野仁一割裂满蒙的言论;给顾颉刚写信,痛斥日本人在暹罗鼓吹桂滇为泰族故地、英国人在缅甸以佛教信仰拉拢云南土司鼓吹立国、署名干城的文章宣称“汉人殖民云南”是鲜血斗争史;再看到他坚决反对给田汝康《摆夷之摆》一书以“研究泰国、越南、缅甸或马来等地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的蚁光炎奖金,是因为云南不可以被视为泰国一样的“外国”,可以体会到,这些有关民族和边疆的学术议论,与国家存亡和民族认同有着莫大关系。一直到1944年1月23日,傅斯年给一个叫做郑细亚的人写信,尽管对方只是一个学界门外汉,但是事关国土,他仍然不厌其烦地向他说明“大清帝国之版图是怎样,民国是满清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并且一一解说“谁把中国土地占去最多”。
在最近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三册中,我看到了这些过去不曾公布的材料,深知这一论述和争辩的重要。那个时代,傅斯年、顾颉刚以及马毅等人,一方面,针对留洋回来的民族学家吴文藻、费孝通仍在国内进行民族识别,甚至承认“中国本部”即传统中国为长城以内十八省的说法,提出严厉批判,说“这是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傅斯年认为这样闹下去,对国家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官方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顾颉刚与马毅一道,在1941年向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二届边疆教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建议订正上古历史汉族驱逐苗族居住黄河流域之传说,以扫除国族团结之障碍案》,从中西融合到确定中国文化本位,从批评帝国主义影响到改变麻醉的学风,从驳斥尧舜禹抹杀论到中国人为黑白混血论,他们在特殊时期,试图重新认识和诠释中国文化,“作成新的历史脉络”、“批判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污染而导致的学界支离灭裂”。
学界的争论风波与来自舆论的压力,也影响了政党与政府。当年的国民政府不仅成立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也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连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也特别要确认教材的“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这一掺入了很多政治关怀和民族情绪的争论,现在当然已经过去,是非曲直也可以重新讨论。但那个时代的民族学和民族史论争,确实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一页。在民族国家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学术不能置身事外,只要读一下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5)、齐思和《民族与种族》(1937)、顾颉刚《中华民族之团结》(1937)、马毅《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1939)等等,就知道这种有关民族、国家、疆域的话题中,有多少政治的关怀。
苗族史研究勾起的感想
在中国,无论是1949以前,还是1949以后,民族、宗教、边疆等等,都是极其复杂、纠缠和敏感的领域,这大概是事关国家统一、民族认同和社会稳定的缘故。本来是学术的话题,总是染上政治的色彩;原本是本土的研究,却躲不开东洋和西洋的阴影;本来是历史的话题,却纠缠着现代各种各样的理论与观念;本来是民族史的事情,却影响了民族史之外各种相关领域的趋向。因此,当我看到日本北海道大学吉开将人教授所著《苗族史の近代》系列论文时,就不免生出一点感想。
《苗族史の近代》所写的,并不是苗族本身自古至今的历史,而是现代中国苗族史研究的学术史。也许,是因为在苗族地区住过很长时间的缘故,每当我看到有关苗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都忍不住要翻一翻。至今,我书柜的显著位置还放着田雯《黔书》、爱必达编《黔南识略》和罗绕典修《黔南职方纪略》。但是,原本这些苗族史的浏览,都是为了追忆往事,虽然我也会用这些资料写一些散文随笔,可始终没有去做苗族史研究的念头。在我心底,苗族与历史,清水江和香炉山,只是青春记忆中的背景,让我想到那一片山,那一片水。
直到2011年3月,在日本东京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苗族史の近代》系列论文,我才意识到,原来苗族史,居然可以串起晚清民国乃至今天这么复杂的民族史、学术史、政治史,而且也与我一直关怀的族群、疆域、认同、宗教以及“中国”有那么深刻的关联。
“汉族西来”与“苗族原住”
追溯到一百年前的晚清民初,在回顾那个时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很多人会注意到“汉族西来说”。为了这个“汉族西来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曾经发生过很大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成为后来学术史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也激活了学术背后的民族立场与国家意识的讨论。但问题是,即使注意到“汉族西来说”,多数学者会忽略这个争论的另一面,“苗族原住说”。可偏偏就是这个“苗族原住说”,以及由此引出的争论,竟然引起了学界的涟漪甚至波涛,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界甚至政界对“民族”问题的观念,从这一点向上追根溯源或向下顺藤摸瓜,能够看到更阔大的政治的、学术的历史世界。
吉开将人教授的《苗族史の近代》,就是从这个晚清民初有关“汉族外来”与“苗族原住”这一说法开始,细细地讨论苗族及其历史研究在近代的流转变化。
众所周知,晚清学界的“汉族西来”说,由拉克伯里(Lacouperie)的《初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和《汉民族以前的中国诸语言》肇端,并通过日本转手传来,这使中国学界深受刺激,当时便引起了好多讨论,这当然跟晚清的大思潮有关。但吉开将人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即如果汉人是西来的,那么中国的原住民又是谁呢?当时的一种说法是,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原住民应当是苗族,由于古史里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因此人们推断,传说中的黄帝打败了蚩尤,就把蚩尤所属的三苗赶走,黄帝代表的汉族人占领了黄河流域中原一带。这种说法的一个大结论就是,苗族才是中国的原住民,而汉族则是外来民族。
吉开将人指出,在19、20世纪之交,一些重要的日本学者,如人类学家里研究过苗族的鸟居龙藏,佛学家高楠顺次郎,法学家田能村梅士,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桑原骘藏等,不知为什么,似乎都接受“汉族西来”与“苗族原住”的说法,这也许有深刻的原因和复杂的背景。
这一论述,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民初思想家们对于国家、民族与疆域的认知。有趣的是,无论是对大清帝国有较深眷念的保守派,还是原本力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派,对这一说法都有热烈的接受者。前者比如梁启超的《中国史序论》(1901)、《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蒋智由的《中国史上旧民族之史影》(1903)、《中国人种考》(1905),后者如章太炎、邹容、陈天华,都曾经接受这种说法。
看上去,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但实际上都有共同之处,即都受到西洋人和东洋人有关民族迁徙的历史观,都承认中国的原住民确实是苗先汉后,但是先进民族最后打败了落后民族。
当然,前者强调的是,既然苗族是更早的中国人,那么,就更应当承认苗族作为土著,应该成为“五族共和”中的一部分;而后者,即建立民国的革命派,虽然原来秉持汉族民族主义的立场,但由于无法承受“割地”、“裂国”的罪名,也不能硬碰硬地靠战争实力解决政权转换,所以也只好采取现实妥协的方法,接受了清帝逊位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提议,立场便从“排斥”转为“包容”。1912年1月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在就职演说中就承诺,为中国领土统一,接受满蒙回藏汉的“民族统一”。
不过,那时的“五族”里面并不包括苗族,这几千万人是否被忽略了?所以,1919年湖南人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就建议,在汉、藏、蒙、满、回之外,加上“苗”,共称为“华族”,一直到1920年代,还有人讨论要五族共和还是六族共和,甚至讨论古代的华族是否混血,是同祖还是不同祖。
学术潮流的背后
吉开将人论文探索的领域开拓得很宽,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甚至波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领域。
比如,最初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以仰韶考古为依据的理论与实践,意在支持“汉族西来说”,但后来的李济、梁思永等人的考古实践,很重要的一条却是要证明,汉族并不是西来的,而是本土各种族群融汇而成的。应当注意到,1928年在哈佛出版的李济的博士论文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试图说明的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出来”,第二章中所说中国人的五个主要成分(黄帝后裔、通古斯族、藏缅语族、勐-高棉、掸语族)与三个次要成分(匈奴、蒙古、侏儒),其实就是在证明中国人是多元种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而同样参与这一潮流,却不是中国人的史禄国,1928年在上海以英文发表的《华北人类学研究》以及两年后发表的《华东与广东人类学研究》,也在说明黄河上游发源的中国人,向东、北、南三个方向发展,但其源头却是一个。正如王道还所说,他们这一历史观念,作为考古学、人类学预设,“无疑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运、世局的一种回应,既是意识形态,也是知识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可以明白,周口店、城子崖、殷墟考古重建的中国历史系谱为什么这么重要,而1920年代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进行西南苗彝调查,前面我们提到的顾颉刚、谭其骧办的《禹贡》、史禄国和杨成志的云南调查,辛树帜、陈锡襄的猺人调查,蔡元培的身兼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主任,1930年代史语所芮逸夫、凌纯声的湖南西部苗族、东北赫哲族调查,也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中去理解。所以,当我们看到芮逸夫早年的《中华国族解》时,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晚年所编的《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三巨册,其实仍然是在这一思路与立场的延长线上。
“外来民族与原著民族之间强胜弱汰图式中的‘汉族西来说’与‘苗族先住说’组合而成的(进化论)历史观渐渐成为遗物,取而代之的,是土著、自生、自律发展为基调的民族本土发展史观,这一史观席卷而来。”正如吉开将人所说,到了1920年代,这些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的新研究,逐渐对这种早期民族迁徙历史产生新的解释模式。1926年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发现、城子崖黑陶文化、殷墟考古,更重建了中国人的自生谱系,只要读读傅斯年《城子崖考古报告》中有关中国古史并非一面,而是多面混合的丰厚文化的论断,就可以明白这一意图,而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3)、蒙文通《古史甄微》(1933)的写作,其实隐隐约约也都与这一思路有关。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学界的某些倾向和潮流,并非空穴来风。那个时候的一些看似考古、看似人类学调查甚至民俗学调查、看似语言学研究的学界活动,其实就是要证明中国是一个多区域、多族群、多宗教合成的一个大国家。前面提到1939年出现的大争论,关键词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里面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为什么傅斯年反对“边疆”这个词,为什么顾颉刚建议废除“中国本部”这个概念,为什么暹罗在日本唆使下改名“Thai”会引起国人的紧张,甚至为什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特别要说中华民族“宗(本)支(枝)”,不是武力政府而是文化同化?这也都可以是从苗族史研究中牵连出来各种大问题。
苗人的反应
更难得的是,吉开将人不仅讨论学界和政界,也关注到苗族(以及夷人)的反应。在第五篇中,他把视角从学界人士转向苗彝人物,其中包括湖南的石板塘(湘西苗族领袖)、石启贵(湘西苗族领袖)、石宏规(湘西苗族领袖)、凉山的岭光电(彝族土司)、曲木藏尧(彝族土司)、云南的龙云、高玉柱(永胜土司)等等。我们看到,一方面,苗族彝族精英的族群意识渐渐滋长,他们批评汉族以他人为夷狄、为猃狁、为蛮貊,要求承认苗彝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在抗日的民族主义背景下,他们也痛斥日本策划伪满洲国,以及帝国主义鼓动西藏、内蒙、回疆的分离倾向,同意汉苗通婚与融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在吉开将人所介绍的苗族精英鼓动的“复兴运动”中,我们看到,这些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为核心支柱的苗族精英们,在重建苗族历史记忆与争取苗族在国家地位的过程中,既受到现代文明的启蒙,接受了现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又努力唤起族群意识,极力在多民族国家中凸显自己民族的角色。
虽然他们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尊德报功而言,在中国的地位当在满蒙回藏之上,但是叙述苗族的很多资料,却来自汉族传统的五经、二十四史;虽然他们整理苗族吟咏先祖和伟人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些民族意识有些又来自西洋人如Samuel Pollard关于“蚩尤为苗人先祖”的启发,也在西洋人的刺激下,以苗歌和芦笙追忆苗族历史;虽然他们顽强地凸显他们的存在,创立西南彝文化促进会(或“西南夷苗代表办事处”),办《新夷族》杂志,但是他们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这个框架,自立的诸多措施,都要争取国民政府的承认;虽然他们不断地要凸显苗族悠久的文化与习俗,但是他们也逐渐接受来自西方甚至是基督教的启发,甚至以苗文印《新约圣经》,还出现了石门坎那样的“最高文化区”。
在民国时期,这些苗族精英渐渐融入国民政府,有的甚至成为国民政府的官员(龙云)或者国大代表,也有一些苗族精英渐渐进入学术界或文化界,成为师范学校的校长(石宏规)或者教师(杨雅各、杨汉先)。在这个时代,致力于掌控国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倒是都注意到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框架下争取苗、彝认同的重要。
“世袭帝国模式”?
我没有看到吉开将人最近发表的第八篇,据说也已经发表。但是仅仅是看前面七篇,内容也很精彩了。如果允许我用简单的方式概括的话,我觉得,第一,他以“苗族史”的研究,串联起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史,而这个学术史过程又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学术在西洋与东洋、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挣扎前行的状况;第二,通过民族史研究的变化,他让我们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变化,包括了极其重要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启蒙优先与救亡优先的嬗变转移;第三,在一个以苗族史研究为主轴的学术史叙述中,它把文化、学术、政治、利害等等都牵涉进去,讨论到了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的疆域、民族、国家以及认同等问题,甚至也涉及晚清民国时期立宪与革命、排满与五族共和、边疆与中央等至关重要的政治和历史问题。
200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近代中国在民族与国家形式上的转变,并非像列文森说的“从天下到万国”,或者徐中约说的“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即它不是从过去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到“国家主义”(Nationalism)转变,中国与欧洲那种“殖民国家式”(colonial national)不同,中国是特别的(或者欧洲是特别的)模式即“世袭帝国式”(Patrimonial imperial)。这个说法是否合理?也许吉开将人以苗族史为案例的讨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回答的线索。(编者删落了全部注释,并加了小标题,敬希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