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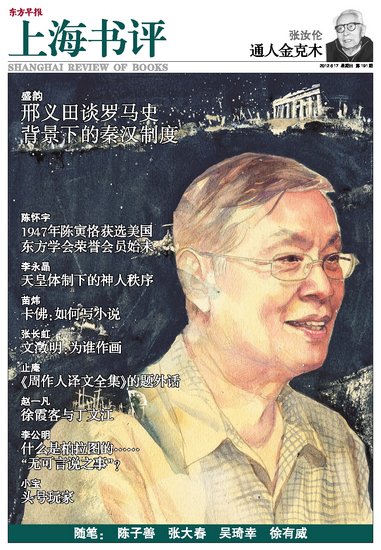
邢义田谈罗马史背景下的秦汉制度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6月17日 记者:盛韵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下发展出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式,这为后人考虑如何治理庞大国家提供了不同的参照体系。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邢义田先生在访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之际,接受了笔者访问,从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比较了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异同。
您对罗马史和秦汉史都有兴趣,注意过两种古文明面临的问题和处理方式,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不同传统。那么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在制度上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邢义田: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背后有不同的传统。秦帝国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在一统中国以前已经有过商、周上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从周人建立封建到春秋战国封建崩溃, 诸国并立,秦也从封建诸侯一变而为争霸的列国之一。照我的看法,秦一统后的帝国制, 有些是原本秦制的延续和扩大,有些是秦始皇的创新, 更有些部分继承了周制。譬如秦在征服过程中,不再分封诸侯, 而是化新征服的土地为郡县; 一统天下后,更将郡县制扩大到了全帝国。这是秦制的延续和扩大。不过,秦始皇很显然又觉得自己超越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周天子的“天子”名号不足以彰显自己的伟大,因而创造了“皇帝”这一新的名号。这是创新。可是秦制有些东西是继承了周以来的传统。比如秦始皇没有放弃自周以来的天命观,也没有放弃周以来天子的称号。他相信自己像周人一样, 是靠老天爷支持得到天下,因而并不觉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来自被统治的百姓。这种周以来的天命观主宰了传统中国两千年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
正因为如此,在古代中国我们就没有看见罗马帝国那样的情形。罗马帝国继承的是一个在地中海世界存在已久的城邦传统。这个城邦传统是希腊城邦建立的。他们基本上相信,城邦的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管理城邦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和承认。城邦的管理者是由公民推选,管理规则和法律须由有管理经验者组成的长老会议提出,经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同意。这种对统治合法性或权力来源的看法和体制,造成了古代地中海城邦世界和古代中国的根本性不同。
罗马人后来统一了地中海世界,由小小的城邦化为庞大的帝国,但保守成性的罗马人仍顽强地维持着共和城邦的传统。罗马在共和时代是一个城邦,已经有公民大会和元老院。组成元老院的元老们是罗马公民的上层阶级,拥有统治权。所有法律和相关政策必须经过元老院的同意。奥古斯都以后,皇帝的身份经元老院认可,才具合法性,皇帝的权力也由元老院制定的法律来规范。元老院颁给即位的皇帝一个法律文件,一条一条订出他有哪些权力。在古代中国,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况。秦帝国和罗马帝国看起来都是大一统帝国,但背后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对权力合法性的认识大不相同,造成两大帝国统治形式的根本性差异。
现在有些人认为秦帝国的官僚体系内部有权力监督和制衡,所以不能算专制……
邢义田:这个在《史记》里记载得很清楚,秦始皇从早到晚,每天要看完一定量的文件才肯休息,文件都要他批过才能算数,丞相都是“备员”而已。既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力量能够限制他,也没有一个人——李斯也好,赵高也好——能制约他。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在政治设计上的一个弱点。在政治设计上中国除了“天命有德”、“灾异示警”和“祖宗之法”这些道德劝说或警告性的东西,不曾建立起足以制约皇权的制度。理论上,皇帝有自天而来至高无上和无限的权力。他要如何施展,就看他怎么做。如果他礼贤下士,决策时愿意和丞相或周边大臣商量,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宋神宗愿意跟王安石“共商国是”,这个时候丞相和大臣才能说得上话;如果像秦皇、汉武这样的人,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就都是司马迁所说的“备员”或摆饰罢了。
尽管有人认为丞相和大臣可以用种种方法削弱或柔化皇帝的专制,例如某官有权批驳皇帝的诏书,或以种种方式达成统治内部的监督和制衡,例如御史、州刺史制等等,但这些制度通常不够坚强,或者说缺乏真正超越人事的制度性保障。制度和法律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没有真正超越性的地位,事随人转或因人设事是更为通常的现象。人治和法治之别,也可以说是秦汉中国和罗马帝国另一个重要的不同吧。罗马人长于法律,直到今天罗马法还是西方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础。传统中国就没这样的东西。法治到今天也还是中国的弱项。
罗马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遇到高卢人、日耳曼人,征服后会遇到对外族人的统治问题,而秦统一后也有如何管理蛮夷的问题,两种文明相对比之下各是如何处理的呢?
邢义田:这个问题的处理倒是有类似性。秦建立郡县制,中央派不同等级的官员做郡县的太守或是县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秦时还有另外一种制度,凡是地方上杂居有蛮夷的,就不设郡县,而设置道。它原来有什么风俗习惯,有什么领袖都得以保存,他们甚至不用像郡县的百姓那样纳税,只要象征性地进贡一些方物特产即可。此外还有所谓的属邦,凡臣属于秦的国家,因其故俗而治,只要顺服,秦对其内部也不加干涉。这种道和属邦的设置,我感觉背后的理念并不是强硬地采取百分之百的同化政策,这跟古罗马帝国有相似的地方。
虽说罗马帝国征服了地中海世界,实际上罗马人采取相当宽容的统治政策。地中海各地本来有很多城邦或城市,罗马人对他们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罗马把除了意大利之外的地方都划为行省,派一位元老去行省当总督。总督基本上只负责收税、保证治安、维持司法秩序。其他方面各省城市都有市议会,由市议会选出的官员管理各自的城市。这些城市只要如数纳税,敬拜皇帝,其原来的习俗和信仰等等都不会受到干扰。因为统治多属象征性的,罗马帝国在三世纪以前从没有建立,也没必要建立像秦汉帝国那么庞大,由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
罗马人甚至不曾像秦始皇一样统一文字。罗马人自己用拉丁文,行政命令用拉丁文发到各地,但不曾要求帝国百姓都用拉丁文。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建立几百年,西半边虽多用拉丁文,东半边的希腊化王国旧地仍以用希腊文为主。此外,我们不要忘了,罗马的贵族自知没有太多文化,不像中国的统治者有非常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罗马人因此不认为自己是文化上的教化者,而是接受别人教化的。他们自始至终卖力地学习希腊文和希腊文化。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野蛮人(即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却又成了希腊的俘虏。”这点跟中国正相反。
罗马帝国在军队上的开销极为庞大,那么军队不打仗的时候干什么?和汉代军队比较呢?
邢义田:这两边的军队性质完全不同。罗马是职业化的常备军,而汉代军队的基本性质比较像民兵,而且中国历朝历代,除了辽、金、蒙古的元、满洲的清,基本上都是如此。齐民百姓有替天子老爷当兵的义务。汉代就规定成年男子必须当一年兵,所谓正卒,一年以后解甲归田当老百姓。只有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要打匈奴了,派几个大将军,临时征召各郡的百姓去参军。仗打完了,将归于朝,兵归于农。
罗马的职业军人一辈子就当兵,那是高度机动的,战斗力非常强,训练非常严格。服役期限也很长,一般军人都要服役二十五年,等于从年轻时候一直当兵到老。如果能够活着退伍,就会获得土地和退伍金等作为回报。它是一个职业,按月领饷,随着年资和功劳,可以升迁或得奖金。
罗马军队的一大问题是不事生产,构成帝国财政上极大的负担。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限,要靠巨大的劳动力投入来维持。国家如果养了一批人不生产而专门消耗,你想想这会对财政造成多大的影响。罗马帝国皇帝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怎么满足军队的需求,除了每个月的薪金,额外的需索也很多。很大程度上说,罗马皇帝的皇位也掌握在军队手里。军队今天喜欢你就推你当皇帝,不喜欢就把你干掉,另推别人上。罗马很多皇帝自己就曾是军团司令,被部队拥立登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职业化、服役时间长,军队成了一个极为强固的利益团体,罗马社会没有可以跟军队抗衡的其他利益团体。所以罗马军队可以在罗马政治史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今天说枪杆子里出政权,罗马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问我罗马军队平时不打仗干啥?除了训练,就干这个。
这样的情形在汉代没有看到,只有到了东汉晚期,因为长期跟匈奴和羌人作战以及黄巾之乱,才出现了长期拥有军队的军阀。像董卓、孙权这样的人掌握了军队,最后使得汉代结束。但在汉代四百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军队都是临时征召,大将也是临时任命,打完仗军队就解散了,将和兵之间没有长久强固的联系,这当然有好处。中国皇帝心里有数,不喜欢将和兵老是粘在一起,对皇权形成威胁。
罗马军队会不会做一些修城墙、修公路之类的公共服务?
邢义田:随着战争的需要,军队行军到一处,最先就要修一个防御性的寨子,以防受到攻击。行军和作战时如果有必要,也会修桥修路,但这些都是为了军队本身和作战的需要而服务,他们不会为老百姓作“公共”服务。我们现在能看到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砖瓦,上面有军团的番号,就知道他们会造房修城。因为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部队,他们自身有很多需要,会自备工匠做很多杂务。但他们不像中国的军队亦兵亦农,“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他们一年到头忙着军事训练,罗马将军的练兵书里有句名言叫:“不能让士兵闲着。”
当兵是自愿的还是义务的?
邢义田:罗马共和时期是公民军,也就是所有公民都有义务为城邦服务,打完仗以后可以回家。可是等到罗马征服了地中海世界,在争霸的过程中因为战事越来越长,比如跟迦太基的战争,一次战役不是一年半载能结束的,士兵没办法解甲归田。共和晚期的士兵已经越来越职业化,到了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后,就彻底成了职业化军队。罗马也从征兵转向了募兵。而且共和晚期许多人会觉得当兵是个好职业,打仗可以分到战利品,如果跟对了军头,可以享尽荣华富贵。恺撒、安东尼都是著名的军头,他们为了争夺政治权力,自己招募军队。这些军队就对他们私人效忠,而非对罗马城邦效忠。这样的军队已失去过去公民军的性质,也谈不上什么义务了。汉代当兵是义务,是所谓徭役的一种。当兵除了每个月拿点口粮,连工资也没有,老百姓都苦哈哈的,被迫去服徭役,所以他们也不觉得是一种光荣,打起仗来谈不上卖力。
经济方面来说,两个帝国赋税体系是怎么样的?
邢义田:罗马帝国相对于秦汉的中国来说是比较松散的,因为罗马没有像中国那么庞大的官僚体系。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西汉末期有官吏十二万多人,可是罗马帝国一直到公元三世纪,在日耳曼蛮族入侵、军队需索不断的外压之下才建立起一种比较庞大的官僚体系,在此之前基本上是城市自治。罗马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统一的财政制度,也没有切实的财税统计,连人口多少都没有具体统一的记录。各城市各有统计,但无需上交中央,只要按时向中央缴纳规定的赋税就可以。所以到今天也没人能搞清楚罗马帝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人口不清,财税收支也一无数字。中国的记录则清清楚楚,全国有多少人口,地方上能收到多少税,有所谓的“上计制”,从地方一层层上报,非常严密。
罗马税制松散,早期则有臭名昭著的包税制——各个行省要收多少税,采用拍卖的方式决定。罗马统治者,主要是骑士阶级的人,可以承包某个行省的税收。比如马其顿省的上缴税收底线是六百万,拍卖时有意承包者竞相出价,他出八百万,你出一千万,没人比你高,这个省就包给你收税。承包人拼命搜刮,最好能收到一千五百万,那多出来的五百万都可以进自己腰包。行省的老百姓因此受尽剥削,却没有公民权。罗马政府利用各省剥削来的钱让罗马公民可以免费看马戏和吃面包。奥古斯都之后才渐渐改变这种状况,派遣总督去各行省,把税额上限固定下来,不再无限制地压榨。
除了行政制度、国家机器之外,还有统治意识形态的问题。罗马帝国有公民的概念,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同意,那么秦汉帝国的统治意识形态是怎样的?
邢义田:对绝大部分传统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有所谓的“政治权利”。孟老夫子这样主张民权的人,经常讲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好像在说老百姓是对国家最最重要的。可是在我看来,他骨子里还是把世界分成两类人,一种是劳心者,一种是劳力者,劳力者只配被统治。他虽主张碰到桀纣这样的暴君时,老百姓有权去推翻他。但在他眼中,老百姓只可乐终,不可虑始,并没有什么能力去成为统治的主体。他们只配劳动, 等待圣王带给他们太平的日子。孟老夫子虽说人皆可为尧舜,但像尧舜这样的圣王五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圣王未出的其他日子,怎么办?孟老夫子没想过,也没给答案。除了他,先秦诸子也都没有想过:老百姓是不是可以不通过流血革命(像周革商的命那样),而以制度性的手段更换他们不喜欢的统治者?先秦诸子虽然主张仁民爱物,以民为本,但压根不认为凡民百姓有能力自治或治人,也压根没有公民治国或公民权的概念。千百年来的中国老百姓只是完粮纳税,柔顺的羔羊而已。
罗马人很早就接触到位于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人所建的殖民城邦,学习了希腊公民治理城邦的观念。公民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有权参加城邦管理,投票选举甚至放逐官员。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雅典就曾发展出一种陶片流放制,只要有六千公民投票,不受欢迎的执政者就会被放逐出雅典十年。罗马人不但早有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在共和晚期可能受到希腊流放制的启发,罗马元老院可以投票,宣布某人为“公敌”,置他于罗马法律保护之外。公敌如果不自动离开罗马,流亡他地,人人得而诛之,财产也会被充公。在共和晚期,这个办法虽然沦为政客政争的工具,无论如何,公民大会或流放制,这些理论上用以保障公民权益的制度,是孟子和所有先秦政治思想家都不曾想过或提出过的。背后意识形态的不同, 由此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先生曾写过《早期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英雄行径》,比较了古希腊的英雄崇拜和早期中国的祖先崇拜传统。您也写过古希腊大力士的形象辗转流传到中土的故事,您觉得英雄的形象对人的集体心理有些什么影响?
邢义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通篇都在表彰英雄,它描述的就是一个英雄的世界。这个世界当然非常男性化,也非常强调武力征服。每个英雄都有大块肌肉,英勇善战,表现出战士和征服者的形象。
中国古代也有英雄,但多数是一种创造文化的英雄,比如燧人氏发明用火,神农氏发明了农业,仓颉发明了文字……读中国的传统典籍,在想象文化发生过程的时候,就会提到什么东西是什么人发明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英雄。虽然也有黄帝大败蚩尤的传说,蚩尤据说能造雾,黄帝于是发明了指南车,他老婆嫘祖更发明了蚕丝。黄帝被强调的形象一直是他夫妻俩如何创造文明,而不是他如何英勇善战。周的开创者文王、武王在革命的过程中也都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但传统上他们被强调的不是如何杀人,而是他们如何举仁义之师,拯救生民,更多的是他们在周公的辅助下,如何制礼作乐,成就周朝伟大的文化。这当然是一种政治神话。讲穿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古书就是古人留下的政治宣传品。一部《尚书》里面很多都是文武周公发出的文告,都在宣传周朝如何得民心,如何替天行道。但古书里也曾留下蛛丝马迹,告诉我们周武王得天下时也曾“血流漂杵”。只是这个部分在周朝宣传部的操纵下,被刻意淡化了,制礼作乐的部分被刻意强化了。为什么几千年来的读书人甘愿接受这样的宣传,反映了怎样的集体心态,不是很值得想想吗?
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秦帝国真正对后世有影响的制度发明。
邢义田:秦的确有一些制度是需要正面肯定的,尽管秦始皇本人的历史形象很负面。要说到对中国有长远影响的,比如说统一文字毫无疑问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修长城当然耗竭民力,但保证了中国农耕地带的安全,后世许多朝代都是靠着长城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到抗战时期,还有西北军大刀队依靠长城抵抗日本人。秦统一后,消除了战国以来各国间的关津壁垒,大修直道和驰道,把很多道路联系起来,成就一个全帝国性的道路系统。这就好像大家形容罗马帝国为“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人在帝国内大修道路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欧洲一直到中古,甚至到近代前期,还在使用罗马时代修筑的不少道路。
此外,我前面提到过,秦帝国的官僚体系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扩大而来,已经经过了长期的试验。秦在征服过程中,以法为治,提高效率,统治体系更为完善有力。秦一统中国后的官僚制度,相对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统治体系来说,无疑是效率最高、最严密的制度。汉承秦制,但记取秦朝短命的教训,刻意除去了秦制中的严苛,增多了合乎人性的成分,例如强调施政须爱惜民力,平民俊秀可为卿相,弱化了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和矛盾。因为这些改进,自汉以来的政治体制才能大体维持了两千年。
长远来看,秦的统一有不可否认的功劳。不过,当时的百姓付出的代价太过高昂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秦十来年就被推翻,合乎情理和正义。后世的人可以轻易不付代价地颂扬秦政,可是不也应该自问:如果活在秦始皇时代的是自己,愿意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