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论文《从百颂体〈弥勒授记经〉来看中印及周边的文化交流》在《复旦学报》2009年第5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发表,以下是文章摘要以及本期栏目“主持人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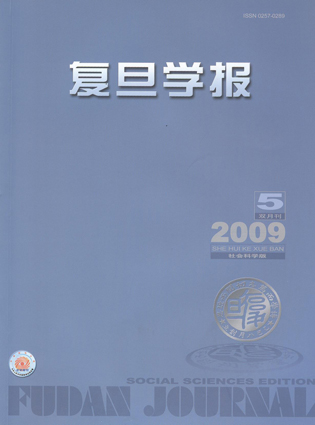
《复旦学报》2009年第5期封面
《从百颂体〈弥勒授记经〉来看中印及周边的文化交流》
刘 震
【摘要】百颂体的《弥勒授记经》是佛教文献中《授记经》系列的最终形式。现存四个梵语本,另有汉文、藏文和波斯文各一个译本。本文拟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文句、内容和产生背景的比对分析,考察同一“母本”在不同的时间、地域和民族间的互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表现形态,进而追寻中印及周边的文化交流痕迹。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弥勒授记经》有梵文、汉文、藏文和波斯文译本,现在发现的四种梵文写本,不仅出土区域不同,抄写的年代也从六世纪一直到十七世纪。《弥勒授记经》流传和翻译的现象说明,在漫长时代里这一关于弥勒的故事贯通了几个不同的地区,也连接了几个不同的文明。刘震先生的这篇文章,主要就是通过对各种写本的描述,来观察中国与印度以及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
用历史学和语言学方法,研究中亚各种民族、宗教与文化的交错,这是十九世纪以来国际东方学的趋向之一。随着当时欧洲列强对亚洲兴趣的增长,也随着欧洲人在中亚的“探险”热,欧洲学者的研究视野陆续拓展,在亚洲腹地新文献的大量出现后,所谓“东方学研究”无论在语言文字、空间范围、历史现象还是关注焦点上,都开始超越了汉族中国,形成现在所说的“西域”这个历史世界,也形成了欧洲东方学的新传统和新方法。同样,随着西洋学术与思想进入东洋,这种亚洲研究,也开始在明治以后的日本兴起,它一方面改变了日本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历史叙述,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这使得明治日本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逐渐形成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而东洋史与中国史相当不同的一点,就是注意满、蒙、回、藏、鲜、越,其中,尤其关注的是“西域”,因为他们要入室操戈,在这个领域中与西洋人争胜。
其实早在清代中晚期,有关西北史地之学就开始在中国学界崛起。十九世纪中叶,这种超越内地十八省空间,也超越三皇五帝历代王朝历史的“绝域与绝学”,一方面作为“考据之学”,一方面作为“实用之学”,逐渐成为学术潮流。特别是,当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到域外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这种学术趋向就激起了传统学术的激变,我曾经把这一变化看成是中国学术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波”,因为无论在视野、工具、文献上看,这都是一个深刻变化,王国维所谓“道、咸之学新”的“新”,就是指这个时代逐渐进入乾嘉诸老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而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也包括所谓的“异族”和“西域”。特别是敦煌、吐鲁蕃等大发现,更促进了“西域”研究,这些千余年之前古文献不仅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而且也由于资料多藏在域外、文献涉及语言繁多、宗教来源成分繁杂、历史地域偏向西侧,迫使学界不得不超越传统,面向国际学界,开出一个新天地。
对各种文字的佛教文献的对勘和研究,就是这一新领域中的重要部分,没有人敢轻视庞大的汉译佛典,也没有人会忽视梵文、巴利文与藏文的佛典,因为从它们之间文意的差异中,恰恰可以寻绎典籍传播中的文化变迁,因而十分值得关注。现在,尽管我们逐渐拥有资料上的便利,但是坦率地说,在这一领域里中国学界的声音还不够大,成果还不够多,这里发表刘震先生这篇论文,表明我们希望中国在这一领域不止是嗡嗡的背景音乐,还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凸出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