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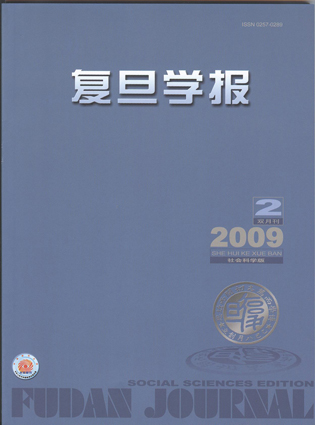
《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本期【主持人语】
《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刊载我院许全胜副研究员《〈西游录〉与〈黑鞑事略〉的版本及研究——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一文,以下为论文摘要,并附本期“文史研究新视野”主持人语。
《西游录》与《黑鞑事略》的版本及研究
——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
许全胜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摘 要】 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和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这两种行记,是研究13世纪上半叶蒙古、西域历史与地理的极其重要的史料。《西游录》元代后就罕有流传,清代仅有节录本存于元人笔记中,得以供学者研究。而日本则保存有旧抄足本,弥足珍贵,它的发现、出版并再传回中国,不仅对研究来说至为重要,而且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黑鞑事略》原刊本也久佚,向无善本,明清间以抄本流传,至近代方有刊本,中日两国学者对此均十分重视。近代大儒沈曾植则是最早为此两种要籍作注的学者之一,沈氏笺注本为作者首先发现并整理研究,其学术价值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视。
葛兆光
本期刊载的是许全胜先生的论文,主题是讨论耶律楚材《西游录》和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以及晚清民初学者沈曾植对它们的注释,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围绕着这两种文献,让我们看到一个领域当它成为国际学界共同话题的时候,知识和文献超越国境的交流情况。
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前半,欧洲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周边即越南、蒙古、朝鲜、印度以及中亚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后来傅斯年所谓“虏学”或学界所谓“西域南海史地之学”,逐渐成为西方中国学的强项,而在明治以后的日本学界,也因为某种政治意图逐渐兴起所谓“满(满洲)、蒙(蒙古)、回(新疆)、藏(西藏)、鲜(朝鲜)之学”。围绕这些区域的研究,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结合的方法,渐渐成了国际东方学界的新潮流。在中国,对于这些“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关注,则一方面来自清代中叶之后逐渐流行的“西北史地之学”,一方面就来自西洋和东洋的这种刺激。尽管现在我们会觉得,这种“预流”有些不情不愿,但是毕竟它使中国逐渐进入了“国际学术语境”,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中国学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一个侧面,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侧面。
在晚清民初中国学人中,沈曾植就是在这些领域中,让西洋学人和东洋学人都敬畏的中国学者之一。虽然许全胜这篇论文只是考证围绕《西游录》和《黑鞑事略》校注和研究的学术史,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学术,尤其是传统中国一直自豪的史地之学渐渐融入国际学界的轨迹。其实,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沈曾植就表现出他对周边史地之学的造诣,所以,难怪他的《圣武亲征录校证》和《蒙古源流考》被金楷理、内藤湖南、那珂通世关注,也难怪他和罗振玉都敢放言,“欧人东方学业尚在幼稚时代”。据说,他曾经告诉王国维“若郅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儿后王之世系”等学问,“一旦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有尚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关诸世界”,这对后来王国维影响甚大,也间接启迪了陈寅恪等学者。后来,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我想,在沈曾植这里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还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似乎同样列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前头。
王国维在贺沈氏七十寿辰的文章中曾说“道咸以降之学新”,所谓“新”,说的就是当时中国一流学者“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已经在西洋东洋学者擅长的领域中入室操戈。尽管当时中国学者在语言能力、图书资料、交通往来条件上尚不很好,但是有一批学者的眼光和笔触,已经涉入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话题,包括古音学、宗教史、边疆四裔舆地、域外碑文与史著等等。可是,在撰《新元史》的柯劭忞、撰《元秘史笺注》的沈曾植和撰《蒙兀儿史记》的屠寄,以及20世纪20年代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陈寅恪,30年代之后倡导边疆史地研究的禹贡学会之后,这一学术潜流究竟走向如何?是“每转益进”而“渐次邃密”,还是“绝学无后”而“终成绝响”?这真是值得回顾的历史。也许,今天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一学脉竟隐没了,什么时候史地之学的方法竟落伍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竟变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