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围绕中国史学史何以“难产”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聚焦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作为专史发展滞后的现象及其深层原因。
梁启超在“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系列演讲中曾感叹道,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本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却长期缺乏史学之专史。他曾规划中国史学史书写的四大核心内容: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达、最近史学之趋势,为后世相关研究奠定了初步框架。但相较于文学史、哲学史等其他专史,中国史学史的系统梳理明显滞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早期代表性著作。结合“新史学”的发展脉络,这一“难产”现象背后涉及学科转型、知识生产、古今中西汇通等多重维度的复杂因素。
中国史学史的系统著作滥觞于20世纪40年代,其中三部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
1941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在自序中坦言“中国史学史,前无作者”,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梳理中国史学特质、史籍类别、史官职守,下编分期叙述自远古至民国的史学发展,注重体裁因创与史家理论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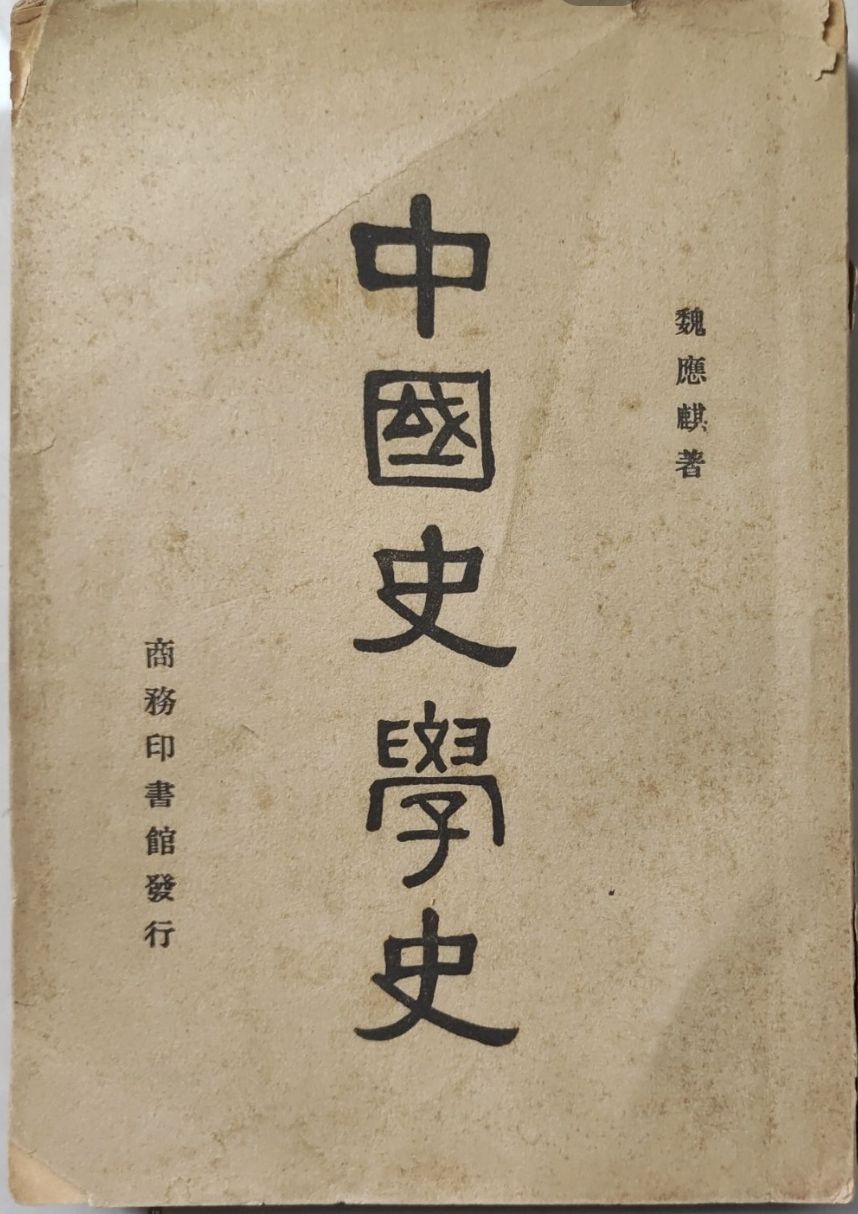
▲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4月版
1941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受梁启超影响最深,金毓黻在日记中记载该书撰写“无可依傍,以意为之”,主要参考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续编》相关论述。全书专用一章讲述“最近史学之趋势”,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和“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两端分析清末至民国的史学变迁,将该时期界定为“史学革新期”,强调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史家的新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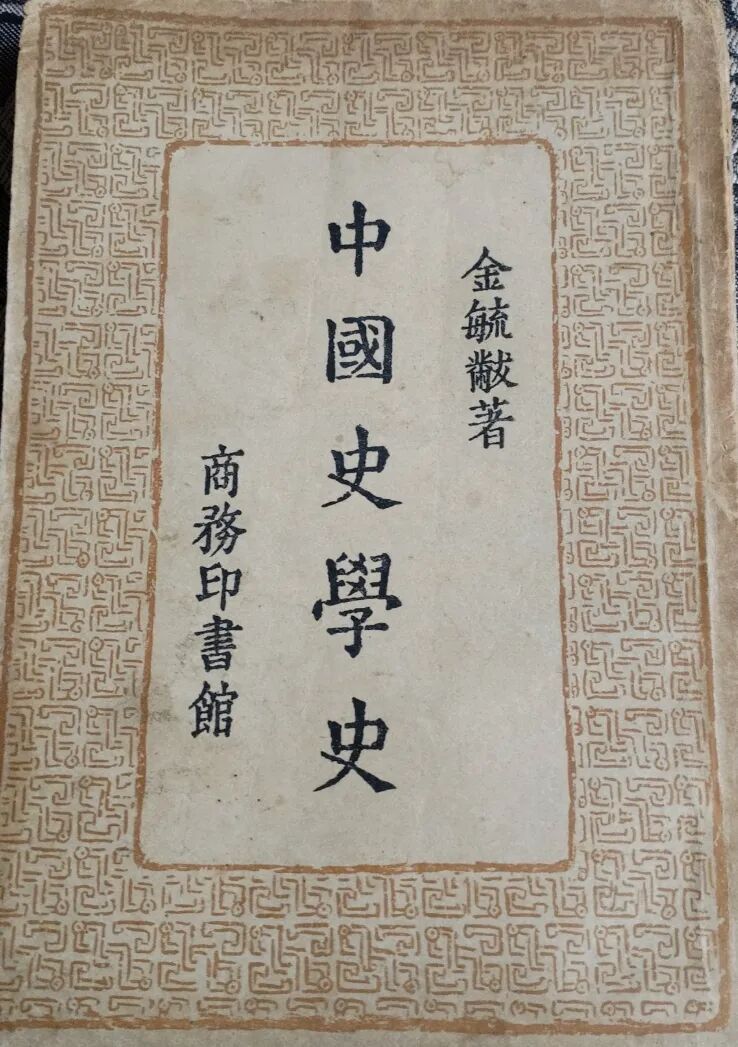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1942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远宗梁启超大义,近取金毓黻著作精华,分史官、史学名著述评、历史体例、历史哲学、近代史学新趋势五大章,形成新的论述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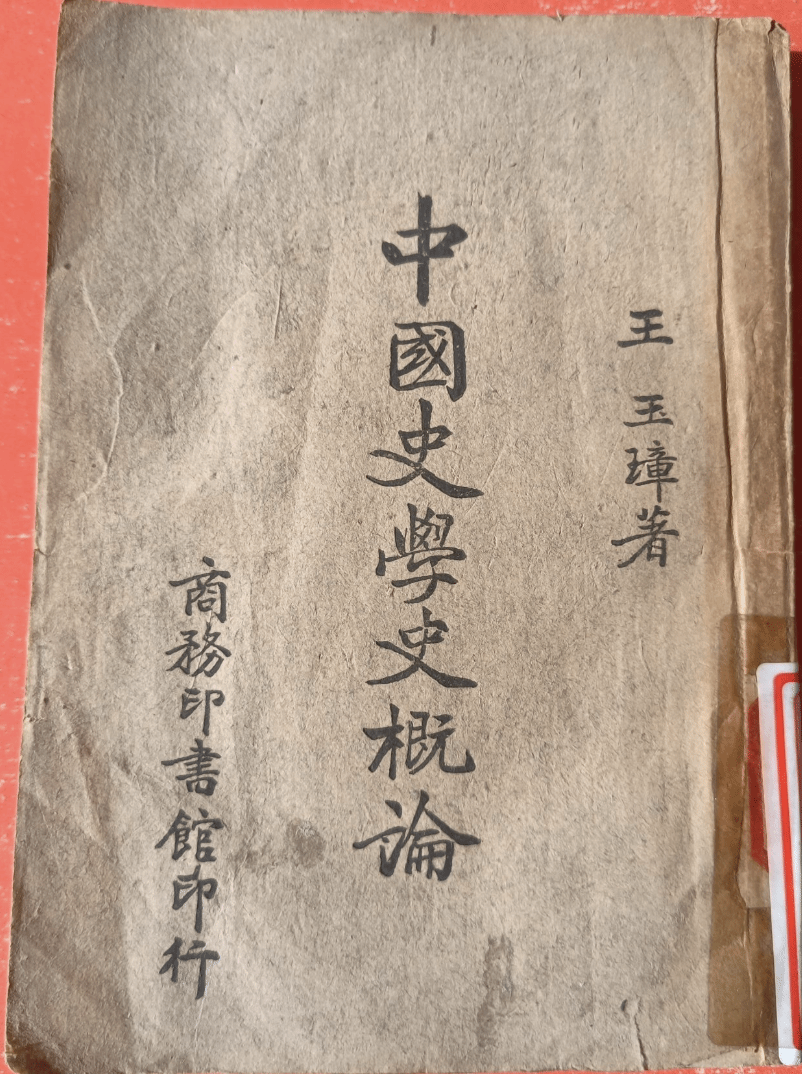
▲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版本不详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晚清民国史学的评述并非晚出。1941年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将中国史学划分为萌芽期、产生期、发展期、转变期四阶段,将清末民初的“新史学”分为“史观派”(含疑古、考古、释古三派)与“史料派”;1945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系统分析民国史学进步的五大助力,包括西洋科学治史方法输入、新史观引入、新材料发现、欧美日本汉学进步、新文学运动兴起,展现了民国时期学者对自身史学发展的及时反思。
相较于其他专史,史学史的滞后性明显。1923年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总结,当时学者已普遍采用西方治学方法整理国故,“洋货”成为治学利器,文学史、哲学史等专史层出不穷,而史学史却长期付之阙如,这种反差构成了报告关注的核心矛盾。
周予同曾提出“通史”的双重含义,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两类“专史”:一类是“学科史”或“学史”,梳理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如哲学史、医学史等;另一类是对应于通史、按社会结构划分的“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
这种分类揭示了近代史学发展的重要转向: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倡导的“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知有局部之史而不知全体之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推动历史范围从“局部”拓展至“全体”,催生了通史与专史的书写需求。伴随分科知识在中国的确立,“各学皆有史”的观念逐渐普及,1898年《格致新报》已提及学问源流的梳理,1905年宋恕明确提出“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为学科史书写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各学皆有史”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史学史却在诸多专史规划中意外缺位:
1905年刘师培《周末学术史总序》依照西方学科分类梳理中国学术,列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等诸多学科史序目,唯独遗漏史学史;国粹学堂的课程设置中,社会学等学科已按古代、中古、近代分期教学,而史学课程仅包含年代学、大事年表、历代兴亡史等内容,未涉及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早期学科史书写中,史学作为“一代学术之总归”的传统定位与近代分科体系产生冲突,导致其在新的学科分类中难以找到明确位置。
这种缺位本质上反映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学科转型的困境:当西方分科体系传入后,原本统摄各类知识的传统史学,在新的学术分类中既要与其他学科区分,又要保持自身的完整性,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导致史学史书写难以起步。
“新史学”对“史学之界说”与“历史之范围”的重新界定,推动史学步入专业化轨道,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章太炎1922年在上海讲国学时坦言“历史本是不能讲的”,二十四史卷帙浩繁,若仅铺排事实或夹杂议论则无甚意义,其国学讲授仅设经学、哲学、文学,未将史学单列。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提出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主张设立“独立史学院”,避免史学被归入文科或理科。这种争议的核心在于,中西历史汇通导致史学范围无限拓展,从传统的政治、人物叙事扩展至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反而使得史学的学科定位变得模糊,直接影响了史学史的书写边界界定。
近代新式教育的推进催生了史学知识生产的新形态,其中教科书编纂成为关键载体,也凸显了史学史书写的困境: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代,试图借鉴西方分期方法解决传统史学“无途辙”的问题,但其核心关注的是历史内容的梳理,而非史学自身的发展;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指出二十四史、《通鉴》等传统史籍不适用于教科,主张“区分时代”“分析事类”,但同样未涉及史学方法、史观演变的系统梳理;
1908年文明书局《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200课时要求,对内容进行精简,强调“列事仅举纲要”,进一步限制了史学史相关内容的纳入。
这些教科书的共同特点是,为适应新式教育需求,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化、简明化,却忽视了对史学自身发展脉络、理论方法演变的梳理。这种知识生产导向使得史学史在教育体系中难以获得足够重视,进一步延缓了其发展进程。
我们认为,近代史学史“难产”的根本症结在于三重张力的难以化解:
中史与西史的张力: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将中国史事与西史分别归入旧学与新学,西方史学的方法、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形成鲜明对立;
无史与有史的张力:20世纪初年“无史”论的浮现,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构成冲击,引发了“中国究竟有无历史”的争论,使得史学史书写的前提受到质疑;
旧史学与新史学的张力:梁启超“新史学”对旧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批判,导致史学界出现严重分歧,新旧史学的界定标准不一,直接影响了史学史的叙事框架。
这三重张力的核心在于,新史学的兴起使得“何为史”“何为史学”的定义发生根本变化,传统史学以史籍编纂、史官制度为核心,而新史学强调“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求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史学史难以形成统一的书写标准。
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史学史著作未能有效解决上述张力: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虽试图融合新旧史学,但其定义的“史学史”既包括传统史籍的法式义例,又涵盖近代史学的进化因果,导致前后论述不一致,遭到白寿彝的严厉批评;齐思和评价该书“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认为其仅关注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与史学演变大势,未能真正把握史学史的核心要义;蔡新枚指出,史学史难产的关键在于“新史学的理论未定型”,学者既缺乏对史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又未能清晰认识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
这种局限并非个例,而是当时史学界的普遍困境。早期学者要么侧重传统史学的梳理而忽视新史学的发展,要么试图融合新旧却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导致史学史著作难以形成系统完备的体系。
其他学科史的书写困境为史学史提供了参照。陈邦贤1919年《中国医学史》试图融合中医与西医,但伍连德在序言中坦言中西医“观察点之各异”,难以真正“方轨并骛”。伍连德与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中,四分之三的内容聚焦近代西医传入,对传统中医仅简略提及。
这种现象与史学史的困境高度相似:当传统学术遭遇西方分科体系,学科史书写要么偏向西方范式而忽视本土传统,要么试图融合却难以找到契合点。这种跨学科的共性问题表明,史学史的“难产”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挑战,其核心在于如何在中西汇通中找到自身的发展路径。
综合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史学作为中国固有学问,在近代学科转型中虽被认为是“中西皆有的一门学科”,但这种认知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转型过程。中国传统史学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其向近代学科的转变,以及与西方史学的汇通,是一个充满张力与争议的过程。
史学史的“难产”本质上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困境的集中体现:它既涉及知识层面的中西融合、新旧对接,又关乎制度层面的学科定位、教育设置,还包含观念层面的史学定义、功能认知。只有理清这些复杂因素,找到新旧史学的汇通之道,才能真正解决史学史的书写难题。
所以,审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不能脱离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也不能忽视学科转型的内在逻辑。史学史的“难产”并非缺陷,而是其在转型过程中不断调适、寻找自身定位的必然阶段,这一过程所展现的张力与困境,恰恰构成了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重要窗口。